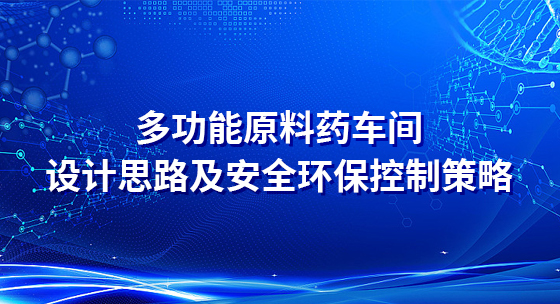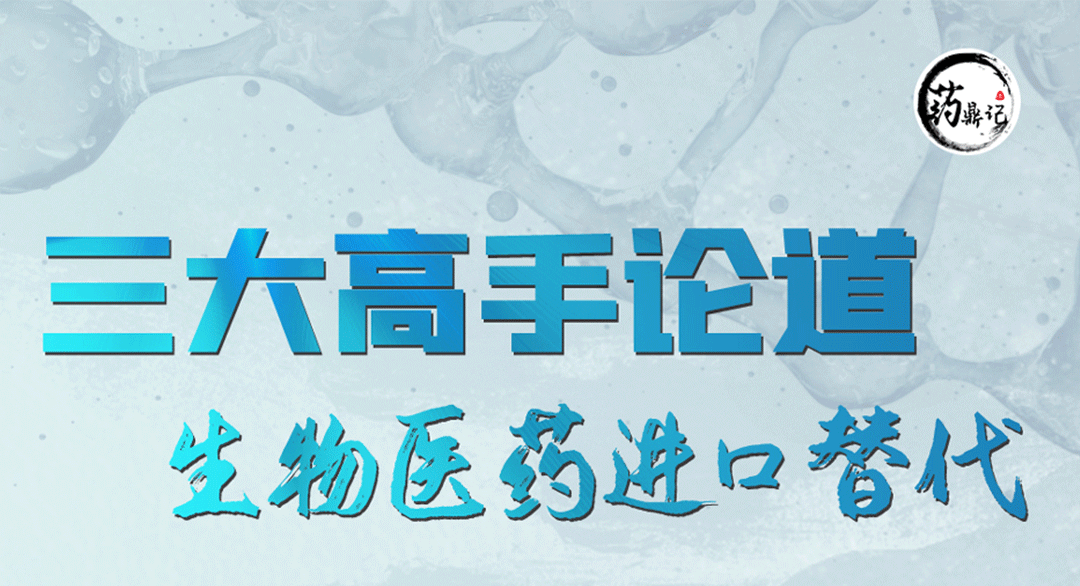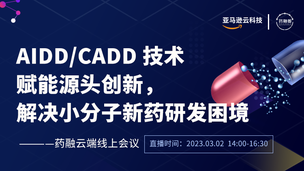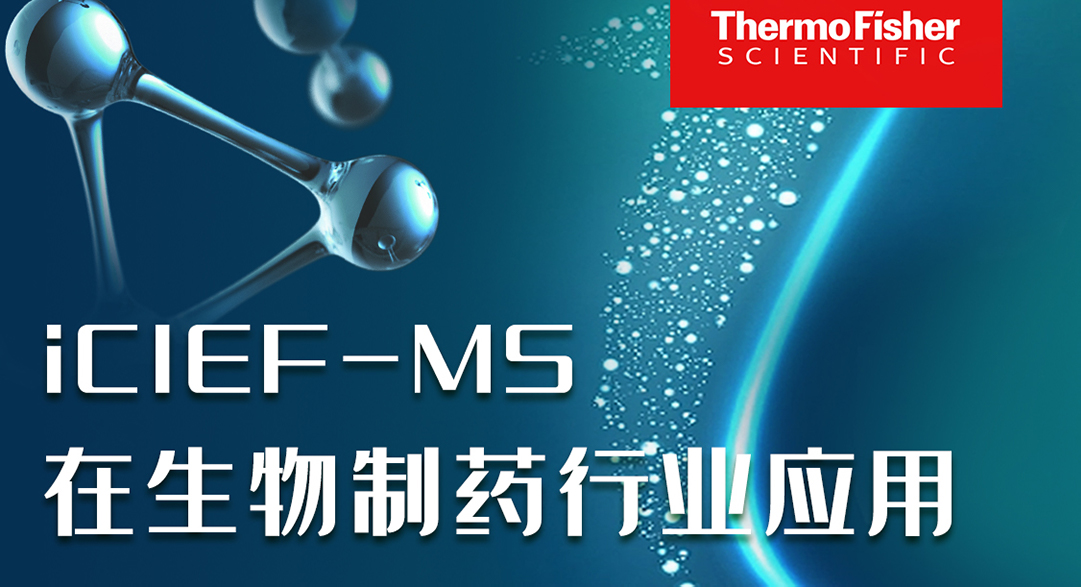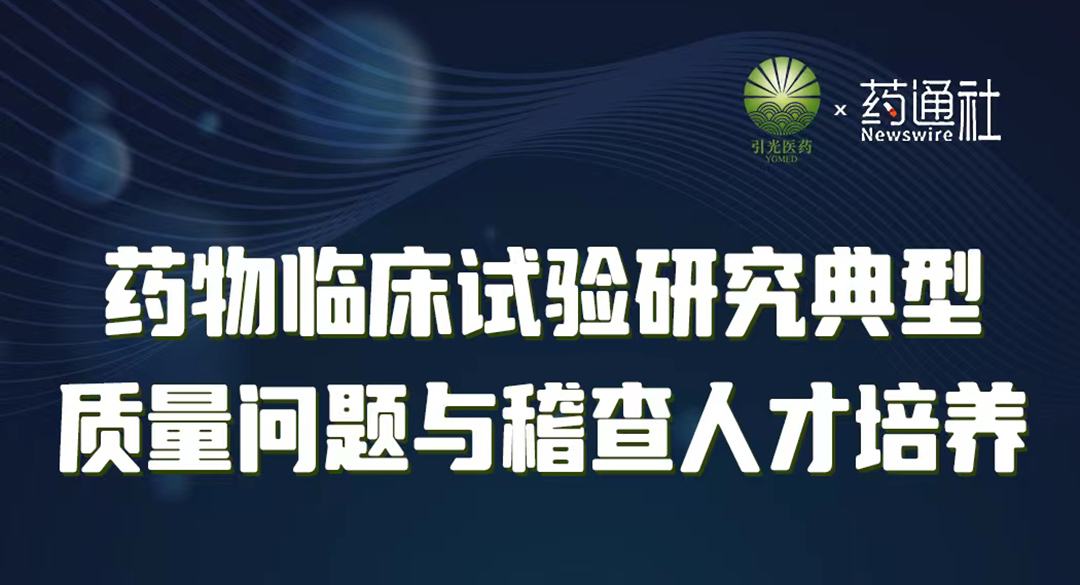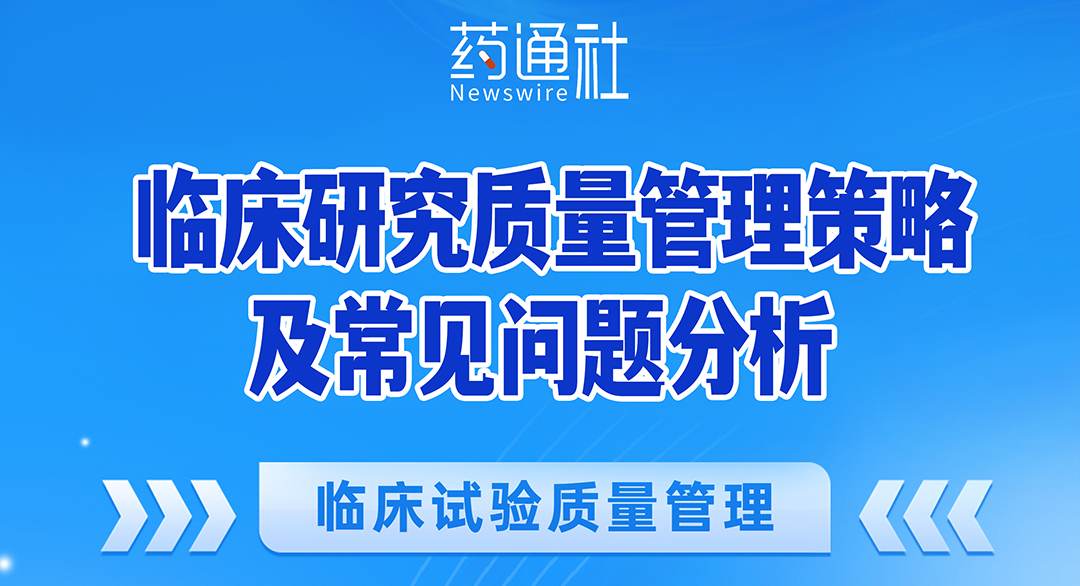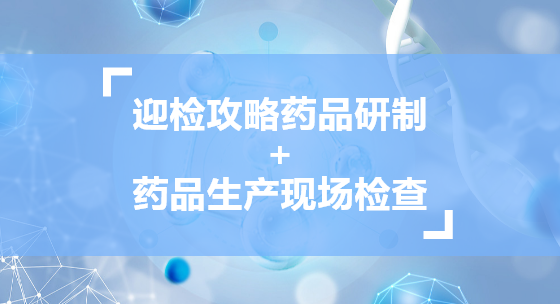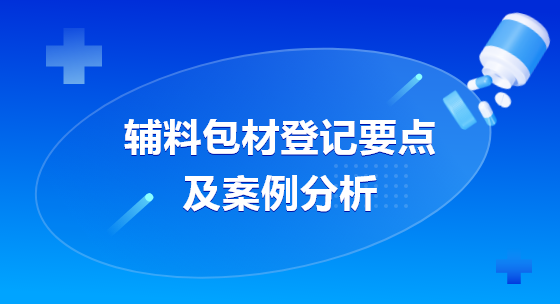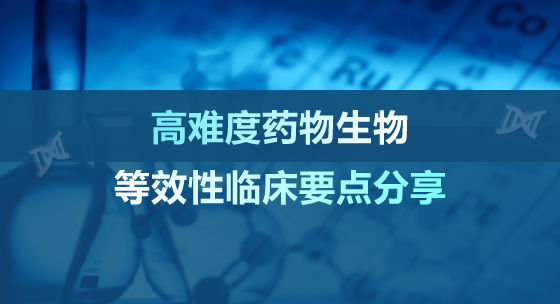药鼎记直播
累积参与直播人次近300W,超500位上市或准上市企业决策层参加
-
 174期:与仿制药CXO创始人交流:畅谈仿制药行业的机遇与前景陈再新、 王二敬、 陶春蕾、 李明丽仿制药5698 2024-06-14
174期:与仿制药CXO创始人交流:畅谈仿制药行业的机遇与前景陈再新、 王二敬、 陶春蕾、 李明丽仿制药5698 2024-06-14 -
 172期:合成生物学引领工业生物制造:生物催化、炼制与食品制造的融合创新朱之光、 李金根、 李德茂、 曲戈生物电催化 技术探讨 食品制造技术 合成生物学 问答 工业生物制造7854 2024-05-31
172期:合成生物学引领工业生物制造:生物催化、炼制与食品制造的融合创新朱之光、 李金根、 李德茂、 曲戈生物电催化 技术探讨 食品制造技术 合成生物学 问答 工业生物制造7854 2024-05-31 -
 171期:再生医学前沿:软组织再生替代,健康护航新时代陈忠华、 孙文全、 潘登科、 魏旭峰再生医学 人体软组织 器官替代治疗 器官定制 问答7750 2024-05-24
171期:再生医学前沿:软组织再生替代,健康护航新时代陈忠华、 孙文全、 潘登科、 魏旭峰再生医学 人体软组织 器官替代治疗 器官定制 问答7750 2024-05-24 -
 170期:2024年改良型新药盘点:开发策略与机遇,分子改良的目标设计与优化张海龙、 盛晓霞、 张哲峰、 占昌友创新药/改良型新药 药物设计6554 2024-05-17
170期:2024年改良型新药盘点:开发策略与机遇,分子改良的目标设计与优化张海龙、 盛晓霞、 张哲峰、 占昌友创新药/改良型新药 药物设计6554 2024-05-17
-
 174期:与仿制药CXO创始人交流:畅谈仿制药行业的机遇与前景陈再新、 王二敬、 陶春蕾、 李明丽仿制药5698 2024-06-14
174期:与仿制药CXO创始人交流:畅谈仿制药行业的机遇与前景陈再新、 王二敬、 陶春蕾、 李明丽仿制药5698 2024-06-14 -
 154期:2024年仿制药走向:预估仿制药未来的发展趋势,探讨仿制药企业该何去何从马路军、 戴萍、 郭新峰、 史凌洋、 江鸿嘉宾介绍 仿制药行业 仿制药企业4357 2024-01-26
154期:2024年仿制药走向:预估仿制药未来的发展趋势,探讨仿制药企业该何去何从马路军、 戴萍、 郭新峰、 史凌洋、 江鸿嘉宾介绍 仿制药行业 仿制药企业4357 2024-01-26 -
 128期:C游记后传:仿制药CRO 2023生存之战欧阳冬生、 张颢腾、 冯胜昔、 田元仿制药4980 2023-07-28
128期:C游记后传:仿制药CRO 2023生存之战欧阳冬生、 张颢腾、 冯胜昔、 田元仿制药4980 2023-07-28
-
 114期:战略领域——细胞治疗CEO圆桌会金华君、 李俊、 张柯细胞治疗 CAR-T TCR-T13685 2023-04-21
114期:战略领域——细胞治疗CEO圆桌会金华君、 李俊、 张柯细胞治疗 CAR-T TCR-T13685 2023-04-21 -
 96期:基因治疗创新年度观点盘点何春艳、 董文吉、 陈懿玮、 肖啸基因治疗3348 2022-12-16
96期:基因治疗创新年度观点盘点何春艳、 董文吉、 陈懿玮、 肖啸基因治疗3348 2022-12-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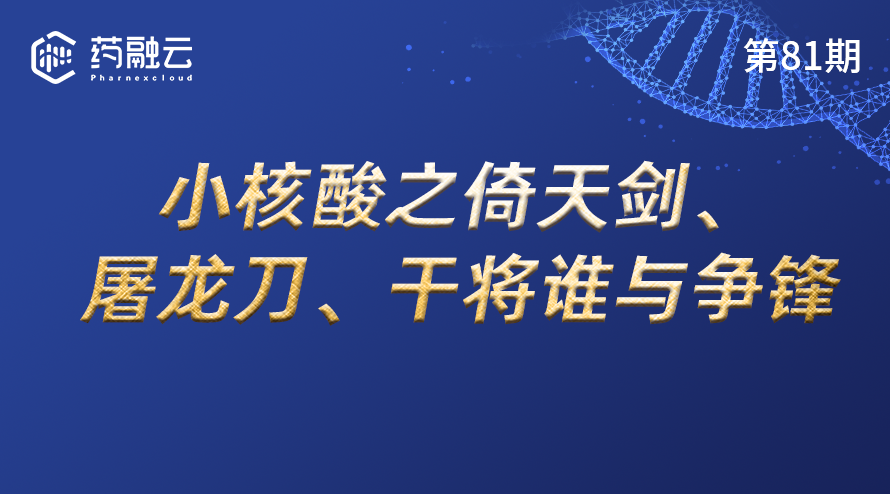 81期:小核酸之倚天剑、屠龙刀、干将谁与争锋王泽峰、 王海盛、 张辰宇新药 仿制药5809 2022-09-02
81期:小核酸之倚天剑、屠龙刀、干将谁与争锋王泽峰、 王海盛、 张辰宇新药 仿制药5809 2022-09-02 -
 68期:溶瘤病毒之天下无瘤杨勇、 刘滨磊、 颜光美、 杨勇溶瘤病毒4968 2022-06-03
68期:溶瘤病毒之天下无瘤杨勇、 刘滨磊、 颜光美、 杨勇溶瘤病毒4968 2022-06-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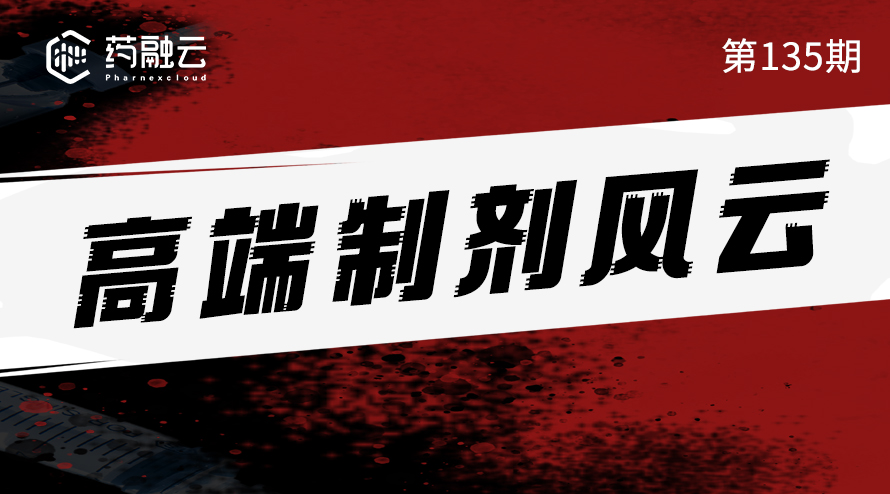 135期:高端制剂风云李永勇、 葛季声、 陈柏州、 刘权制剂 可溶性微针 仿制药6940 2023-09-15
135期:高端制剂风云李永勇、 葛季声、 陈柏州、 刘权制剂 可溶性微针 仿制药6940 2023-09-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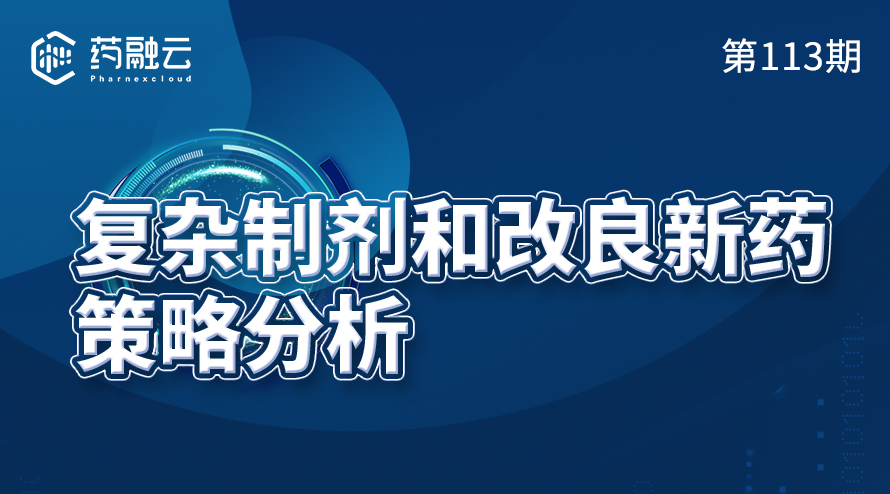 113期:复杂制剂和改良新药策略分析程泽能、 魏世峰、 张严源、 谭重庆制剂 改良新药3303 2023-04-14
113期:复杂制剂和改良新药策略分析程泽能、 魏世峰、 张严源、 谭重庆制剂 改良新药3303 2023-04-14 -
 104期:拼杀高端制剂2.0杨帆、 全丹毅、 陈钢制剂3008 2023-02-10
104期:拼杀高端制剂2.0杨帆、 全丹毅、 陈钢制剂3008 2023-02-10 -
 97期:神雕侠侣之“苗”王争霸刘勇、 严景华、 郑秀玉、 李航文、 徐龙、 陈毅歆、 陈凌、 吴克疫苗创新3309 2022-12-23
97期:神雕侠侣之“苗”王争霸刘勇、 严景华、 郑秀玉、 李航文、 徐龙、 陈毅歆、 陈凌、 吴克疫苗创新3309 2022-12-23
-
 99期:预见XDC,万物皆可联李锦才、 朱忠远、 秦刚、 薛彤彤、 徐寒梅抗体药2896 2023-01-06
99期:预见XDC,万物皆可联李锦才、 朱忠远、 秦刚、 薛彤彤、 徐寒梅抗体药2896 2023-01-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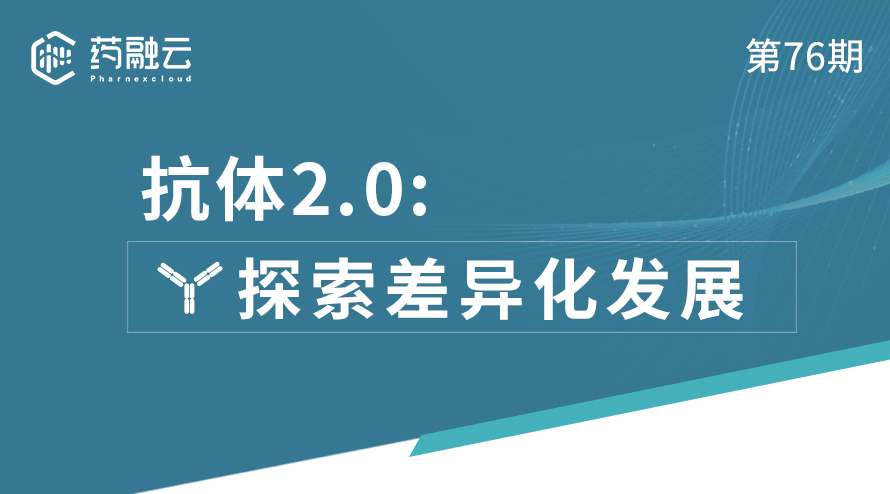 76期:抗体2.0:探索差异化发展殷刘松、 薛彤彤、 沈月雷、 马宁宁抗体药4821 2022-07-29
76期:抗体2.0:探索差异化发展殷刘松、 薛彤彤、 沈月雷、 马宁宁抗体药4821 2022-07-29 -
 73期:决战抗体赛道方磊、 李浩强、 李景荣、 李润生创新转型 制剂5717 2022-07-08
73期:决战抗体赛道方磊、 李浩强、 李景荣、 李润生创新转型 制剂5717 2022-07-08 -
 67期:抗体药风云录朱义、 康小强、 李自强抗体药 立项 新药4899 2022-05-27
67期:抗体药风云录朱义、 康小强、 李自强抗体药 立项 新药4899 2022-05-27
-
 172期:合成生物学引领工业生物制造:生物催化、炼制与食品制造的融合创新朱之光、 李金根、 李德茂、 曲戈生物电催化 技术探讨 食品制造技术 合成生物学 问答 工业生物制造7854 2024-05-31
172期:合成生物学引领工业生物制造:生物催化、炼制与食品制造的融合创新朱之光、 李金根、 李德茂、 曲戈生物电催化 技术探讨 食品制造技术 合成生物学 问答 工业生物制造7854 2024-05-31 -
 169期:与医美创始人近距离交流,了解医美行业那些事夏添、 丁威、 周俊芳、 任坤医美产品 医美赛道5303 2024-05-10
169期:与医美创始人近距离交流,了解医美行业那些事夏添、 丁威、 周俊芳、 任坤医美产品 医美赛道5303 2024-05-10 -
 166期:进口替代辅料:药用辅料市场的新趋势与现状分享何飞、 赵军、 杨学成、 李三鸣药用辅料 新质生产力 市场行情 问答6868 2024-04-19
166期:进口替代辅料:药用辅料市场的新趋势与现状分享何飞、 赵军、 杨学成、 李三鸣药用辅料 新质生产力 市场行情 问答6868 2024-04-19 -
 155期:中国药用辅料探索:如何寻找优质辅料?吉民、 段民英、 王岩松药用辅料 嘉宾介绍 微晶纤维素 纳米制剂 药物递送5436 2024-02-02
155期:中国药用辅料探索:如何寻找优质辅料?吉民、 段民英、 王岩松药用辅料 嘉宾介绍 微晶纤维素 纳米制剂 药物递送5436 2024-02-02
-
 148期:生物药CMC讨论:生物药CMC上下游,生物药CMC工艺方 法,药明生物CMC项目马宁宁、 苏建华、 刘丁、 胡炜炜、 李锋生物药 上下游 CMC工艺4495 2023-12-15
148期:生物药CMC讨论:生物药CMC上下游,生物药CMC工艺方 法,药明生物CMC项目马宁宁、 苏建华、 刘丁、 胡炜炜、 李锋生物药 上下游 CMC工艺4495 2023-12-15 -
 146期:合成生物学造万物刘波、 郝玉杰、 周洁合成生物学 问答5053 2023-12-01
146期:合成生物学造万物刘波、 郝玉杰、 周洁合成生物学 问答5053 2023-12-01 -
 111期:合成生物学造万物4尹洁、 夏霖、 王雪峰、 范开、 于大禹合成生物学 生物学2863 2023-03-31
111期:合成生物学造万物4尹洁、 夏霖、 王雪峰、 范开、 于大禹合成生物学 生物学2863 2023-03-31 -
 93期:合成生物学圆桌谈杨世辉、 王勇、 郑高伟、 郭美锦抗体药 新药4924 2022-11-25
93期:合成生物学圆桌谈杨世辉、 王勇、 郑高伟、 郭美锦抗体药 新药4924 2022-11-25
-
 170期:2024年改良型新药盘点:开发策略与机遇,分子改良的目标设计与优化张海龙、 盛晓霞、 张哲峰、 占昌友创新药/改良型新药 药物设计6554 2024-05-17
170期:2024年改良型新药盘点:开发策略与机遇,分子改良的目标设计与优化张海龙、 盛晓霞、 张哲峰、 占昌友创新药/改良型新药 药物设计6554 2024-05-17 -
 162期:两大偶联药物探讨:ADC与RDC的特点及应用前景蔡家强、 洪浩、 刘谦、 张一帆嘉宾介绍 纳米抗体 药物研究 ADC 药物研发 创新药研发 新药技术7477 2024-03-22
162期:两大偶联药物探讨:ADC与RDC的特点及应用前景蔡家强、 洪浩、 刘谦、 张一帆嘉宾介绍 纳米抗体 药物研究 ADC 药物研发 创新药研发 新药技术7477 2024-03-22 -
 160期:深度剖析中药创新:中药创新产品与技术探讨马春波、 王文佳、 曹明成、 钱勇嘉宾介绍 中药创新药 工艺开发4120 2024-03-08
160期:深度剖析中药创新:中药创新产品与技术探讨马春波、 王文佳、 曹明成、 钱勇嘉宾介绍 中药创新药 工艺开发4120 2024-03-08 -
 159期:与新药创新者对话:新药研发案例探讨杜新、 康心汕、 樊后兴、 王春河、 娄实嘉宾介绍 新药案例 新药项目4429 2024-03-01
159期:与新药创新者对话:新药研发案例探讨杜新、 康心汕、 樊后兴、 王春河、 娄实嘉宾介绍 新药案例 新药项目4429 2024-03-01
-
 163期:外用制剂盘点:外用制剂的开发挑战与临床应用刘亚利、 吴正红、 汤秀珍、 谷丽外用制剂3241 2024-03-29
163期:外用制剂盘点:外用制剂的开发挑战与临床应用刘亚利、 吴正红、 汤秀珍、 谷丽外用制剂3241 2024-03-29 -
 109期:纳米制剂线上大讨论申有青、 董正亚、 佐建锋、 龙晓英纳米技术2983 2023-03-17
109期:纳米制剂线上大讨论申有青、 董正亚、 佐建锋、 龙晓英纳米技术2983 2023-03-17 -
 84期:制剂下一站创新张哲峰、 辛海量、 蔡孟杰、 刘爱军制剂5187 2022-09-23
84期:制剂下一站创新张哲峰、 辛海量、 蔡孟杰、 刘爱军制剂5187 2022-09-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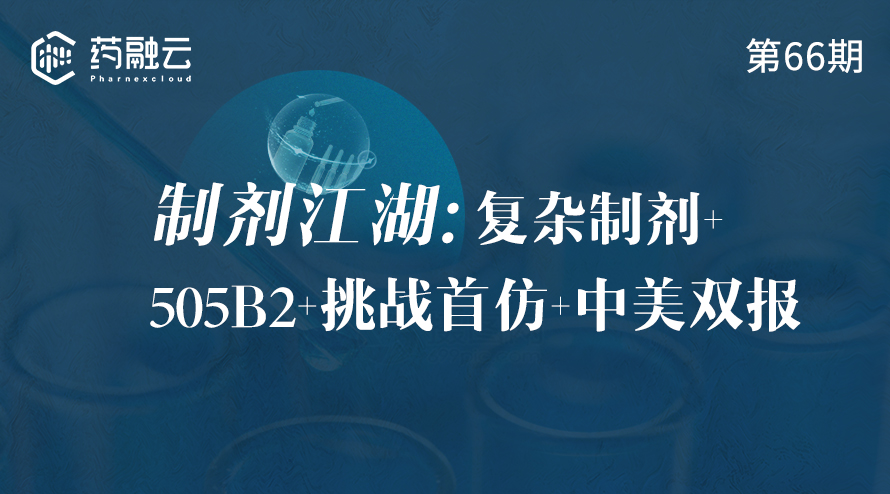 66期:制剂江湖: 复杂制剂+505B2+挑战首仿+中美双报刘荣、 汤丽娟、 徐百制剂 脂质体5153 2022-05-20
66期:制剂江湖: 复杂制剂+505B2+挑战首仿+中美双报刘荣、 汤丽娟、 徐百制剂 脂质体5153 2022-05-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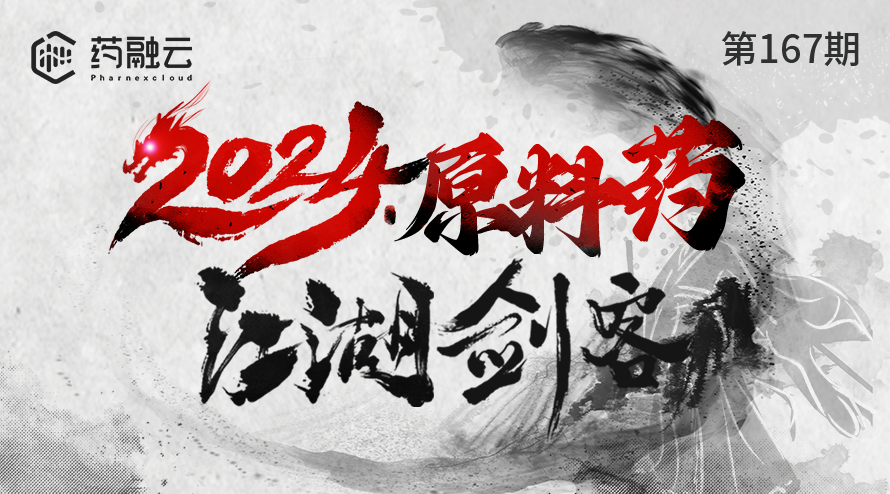 167期:2024原料药行业探讨:原料药国内外行情分析,洞察原料药行业发展趋势叶伟平、 刘国柱、 张颢腾、 高明嘉宾介绍 原料药行业 问答3818 2024-04-26
167期:2024原料药行业探讨:原料药国内外行情分析,洞察原料药行业发展趋势叶伟平、 刘国柱、 张颢腾、 高明嘉宾介绍 原料药行业 问答3818 2024-04-26 -
 150期:2023年度小分子原料行业发展盘点:小分子原料现状,小分子原料CDMO李刚、 阿不都赛米·马木提、 马士忠、 陈仁尔、 陈维华小分子原料5600 2023-12-29
150期:2023年度小分子原料行业发展盘点:小分子原料现状,小分子原料CDMO李刚、 阿不都赛米·马木提、 马士忠、 陈仁尔、 陈维华小分子原料5600 2023-12-29 -
 123期:CPHI大盘点 原料药风云录程志刚、 叶华华、 叶伟平、 马建国、 马建国原料药6368 2023-06-23
123期:CPHI大盘点 原料药风云录程志刚、 叶华华、 叶伟平、 马建国、 马建国原料药6368 2023-06-23 -
 100期: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段继东、 初虹、 程志刚、 王磊原料药3132 2023-01-13
100期: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段继东、 初虹、 程志刚、 王磊原料药3132 2023-01-13
-
 147期:突破内卷:中国药企如何开拓海外市场,解析海外市场准入问题,制定海外市场推广策略吴仙明、 梁健、 荆士恒、 李文胜、 吴莹莹制剂出海 海外市场 观点5596 2023-12-08
147期:突破内卷:中国药企如何开拓海外市场,解析海外市场准入问题,制定海外市场推广策略吴仙明、 梁健、 荆士恒、 李文胜、 吴莹莹制剂出海 海外市场 观点5596 2023-12-08 -
 08期:日本医药解读:日本医药公司分析,日本医药市场规模与现状陆文俊、 中澤肖鋼日本医药4741 2021-04-02
08期:日本医药解读:日本医药公司分析,日本医药市场规模与现状陆文俊、 中澤肖鋼日本医药4741 2021-04-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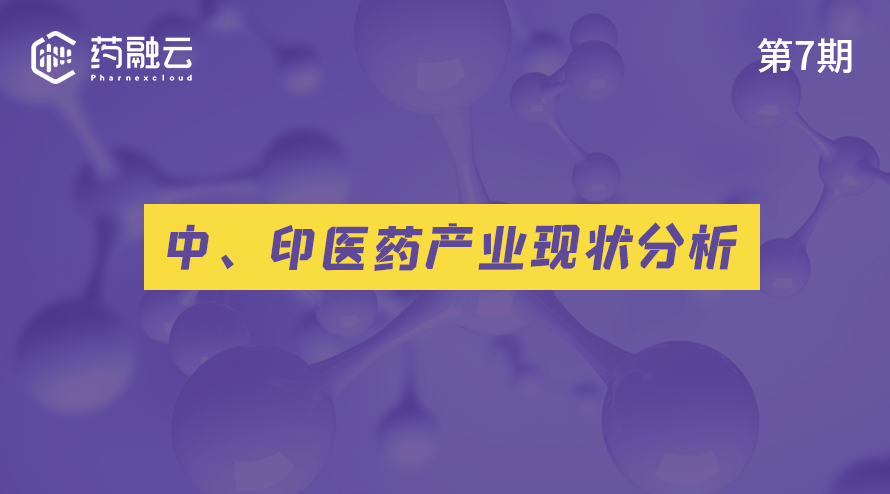 07期:了解印度医药:印度医药产业现状,印度医药企业趋势,中印医药竞争态势Echo、 李金亮医药外贸平台4846 2021-03-26
07期:了解印度医药:印度医药产业现状,印度医药企业趋势,中印医药竞争态势Echo、 李金亮医药外贸平台4846 2021-03-26 -
 23期:中非医药市场 合作新机遇分析李文胜、 严军、 张熊中非市场4786 2021-07-16
23期:中非医药市场 合作新机遇分析李文胜、 严军、 张熊中非市场4786 2021-07-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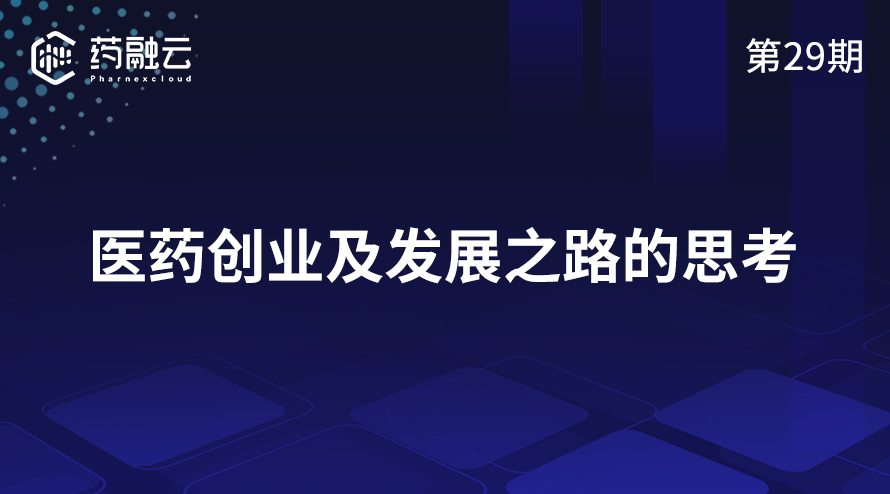 29期:脑洞型科学创业者刘建、 王小龙、 张富尧创新转型4811 2021-08-27
29期:脑洞型科学创业者刘建、 王小龙、 张富尧创新转型4811 2021-08-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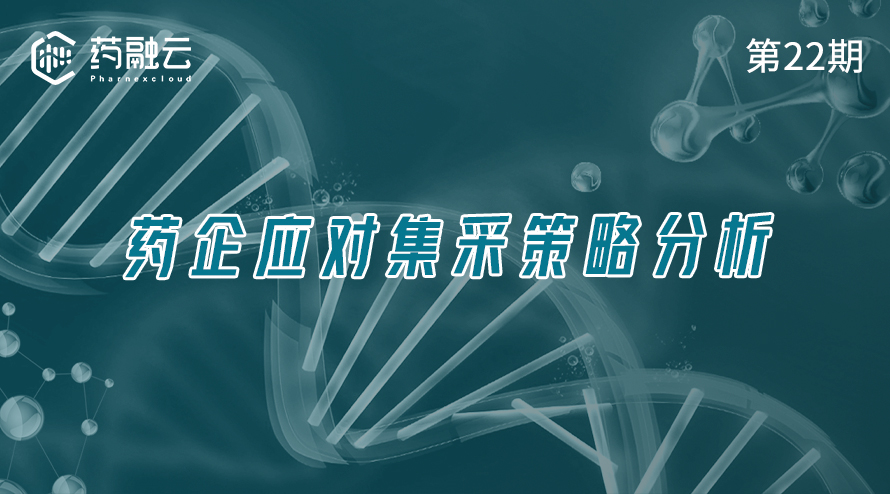 22期:药企应对集采策略分析1耿鸿武、 莫元昭、 张廷杰集采4931 2021-07-09
22期:药企应对集采策略分析1耿鸿武、 莫元昭、 张廷杰集采4931 2021-07-09 -
 09期:药企转型之路:中国医药改革,药企转型方向李晓祥、 汤怀松药企转型4986 2021-04-09
09期:药企转型之路:中国医药改革,药企转型方向李晓祥、 汤怀松药企转型4986 2021-04-09 -
 05期:全球疫情下的医药外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政策,医药外贸市场分析,加强国内外医药贸易合作谭满芳、 班艳、 金春梅、 潘立药融云数据库4586 2021-03-12
05期:全球疫情下的医药外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政策,医药外贸市场分析,加强国内外医药贸易合作谭满芳、 班艳、 金春梅、 潘立药融云数据库4586 2021-03-12
-
 171期:再生医学前沿:软组织再生替代,健康护航新时代陈忠华、 孙文全、 潘登科、 魏旭峰再生医学 人体软组织 器官替代治疗 器官定制 问答7750 2024-05-24
171期:再生医学前沿:软组织再生替代,健康护航新时代陈忠华、 孙文全、 潘登科、 魏旭峰再生医学 人体软组织 器官替代治疗 器官定制 问答7750 2024-05-24 -
 165期:GLP-1靶点药物研发前沿分享:深入探讨GLP-1受体激动剂的现状与发展温晓芳、 刘日勇、 陈伟、 陈小新、 姚元山嘉宾介绍 GLP-1药物 技术探讨5349 2024-04-12
165期:GLP-1靶点药物研发前沿分享:深入探讨GLP-1受体激动剂的现状与发展温晓芳、 刘日勇、 陈伟、 陈小新、 姚元山嘉宾介绍 GLP-1药物 技术探讨5349 2024-04-12 -
 164期: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及其创新应用肖延铭、 丁威、 朱希强、 龚劲松嘉宾介绍 合成生物学 腈水解酶 合成生物学技术8692 2024-04-05
164期: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及其创新应用肖延铭、 丁威、 朱希强、 龚劲松嘉宾介绍 合成生物学 腈水解酶 合成生物学技术8692 2024-04-05 -
 161期:合成生物学的前沿与应用探讨:合成生物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郭美锦、 刘想、 邹祥、 肖延铭嘉宾介绍 合成生物学 酶进化7295 2024-03-15
161期:合成生物学的前沿与应用探讨:合成生物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郭美锦、 刘想、 邹祥、 肖延铭嘉宾介绍 合成生物学 酶进化7295 2024-03-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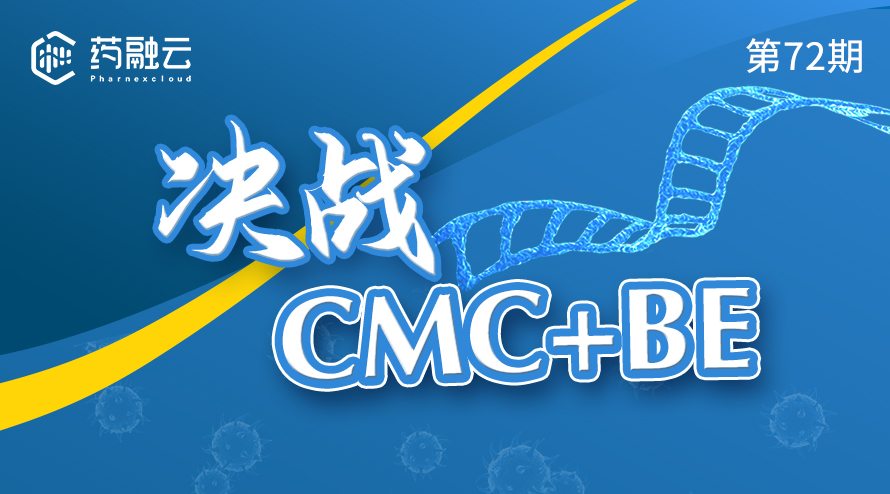 72期:决战CMC+BE雷继锋、 黎维勇、 严子梦绿色制药 创新转型5459 2022-07-01
72期:决战CMC+BE雷继锋、 黎维勇、 严子梦绿色制药 创新转型5459 2022-07-01 -
 44期:CXO之路刘宇晶、 欧阳冬生、 王廷春CXO4903 2021-12-10
44期:CXO之路刘宇晶、 欧阳冬生、 王廷春CXO4903 2021-12-10 -
 13期:CXO产业发展之路楼金芳、 孙建、 杨涛、 殷岚医药外贸平台4758 2021-05-07
13期:CXO产业发展之路楼金芳、 孙建、 杨涛、 殷岚医药外贸平台4758 2021-05-07 -
 33期:CXO赛道实操落地分享刘学军、 陶春蕾、 王元CXO4753 2021-09-24
33期:CXO赛道实操落地分享刘学军、 陶春蕾、 王元CXO4753 2021-09-24
-
 抑郁药物研发探讨:解析抑郁的作用机制与预测抑郁症药物未来走向刘佳凝、 陈椰林、 向家宁、 周显波、 文永顺抑郁症 创新药3654 2024-06-16
抑郁药物研发探讨:解析抑郁的作用机制与预测抑郁症药物未来走向刘佳凝、 陈椰林、 向家宁、 周显波、 文永顺抑郁症 创新药3654 2024-06-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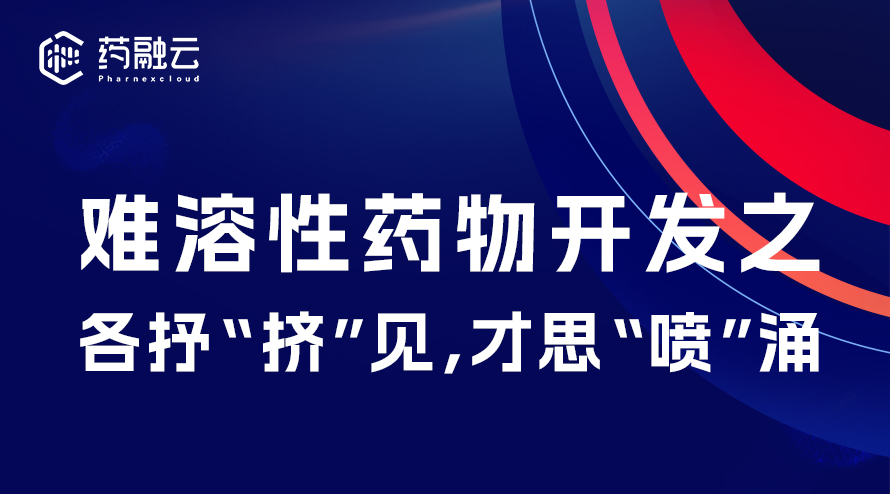 难溶性药物开发探讨:喷雾干燥、双螺杆技术与固体制剂处方工艺解析邹存彬、 冀杨、 何训贵难溶性药物 喷雾干燥技术 双螺杆技术3269 2024-06-12
难溶性药物开发探讨:喷雾干燥、双螺杆技术与固体制剂处方工艺解析邹存彬、 冀杨、 何训贵难溶性药物 喷雾干燥技术 双螺杆技术3269 2024-06-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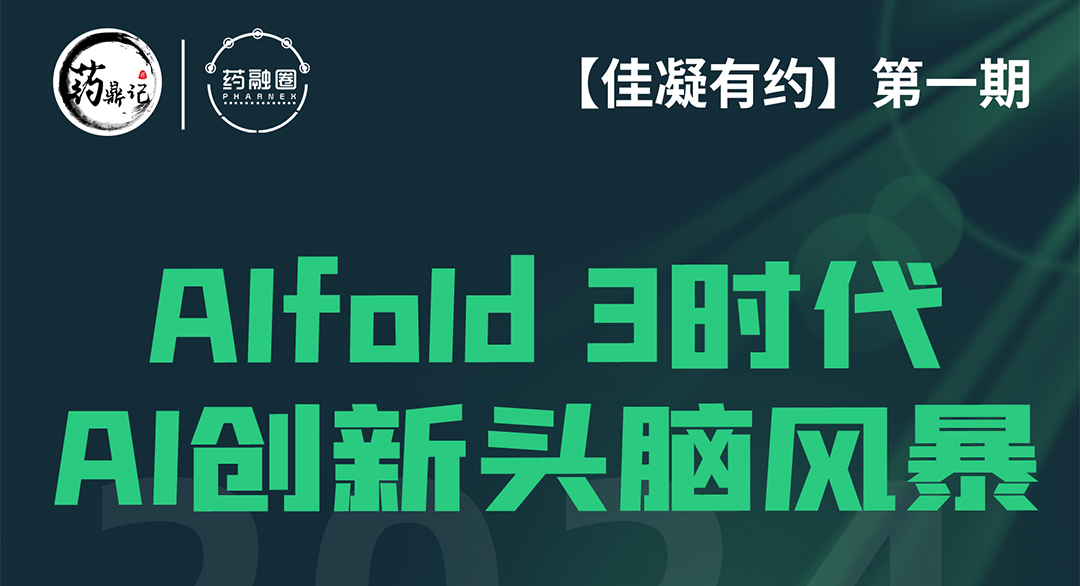 AlphaFold3时代:革新新药研发,引领生物医药新篇章刘佳凝、 何骑、 李小兵、 裴剑锋、 王靖方AI制药2698 2024-05-26
AlphaFold3时代:革新新药研发,引领生物医药新篇章刘佳凝、 何骑、 李小兵、 裴剑锋、 王靖方AI制药2698 2024-05-26 -
 医药出海新动向:拉美市场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Julian Oscar Efler拉美市场3654 2024-05-23
医药出海新动向:拉美市场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Julian Oscar Efler拉美市场3654 2024-05-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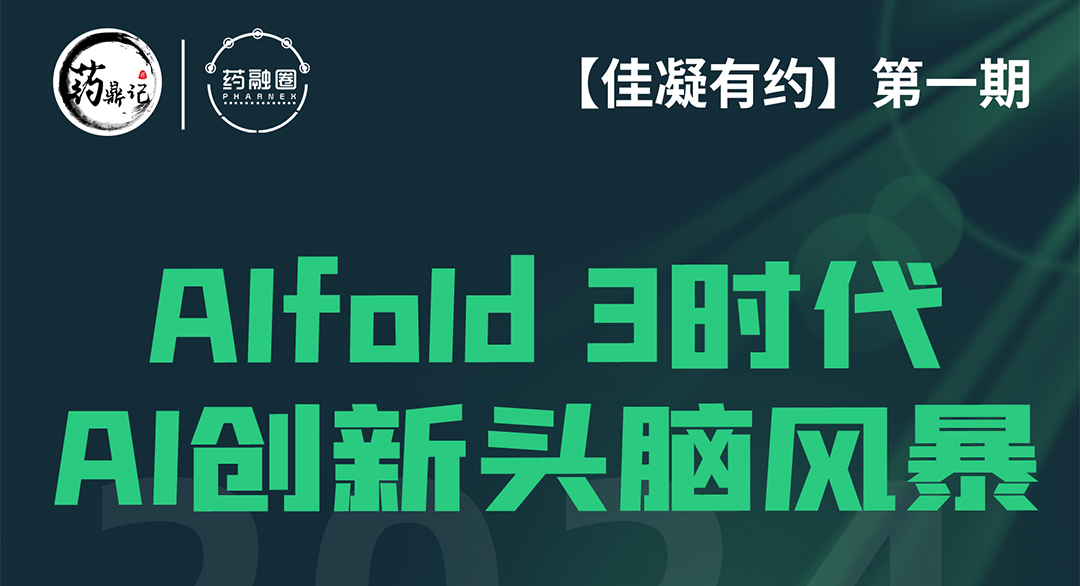 AlphaFold3时代:革新新药研发,引领生物医药新篇章刘佳凝、 何骑、 李小兵、 裴剑锋、 王靖方AI制药2698 2024-05-26
AlphaFold3时代:革新新药研发,引领生物医药新篇章刘佳凝、 何骑、 李小兵、 裴剑锋、 王靖方AI制药2698 2024-05-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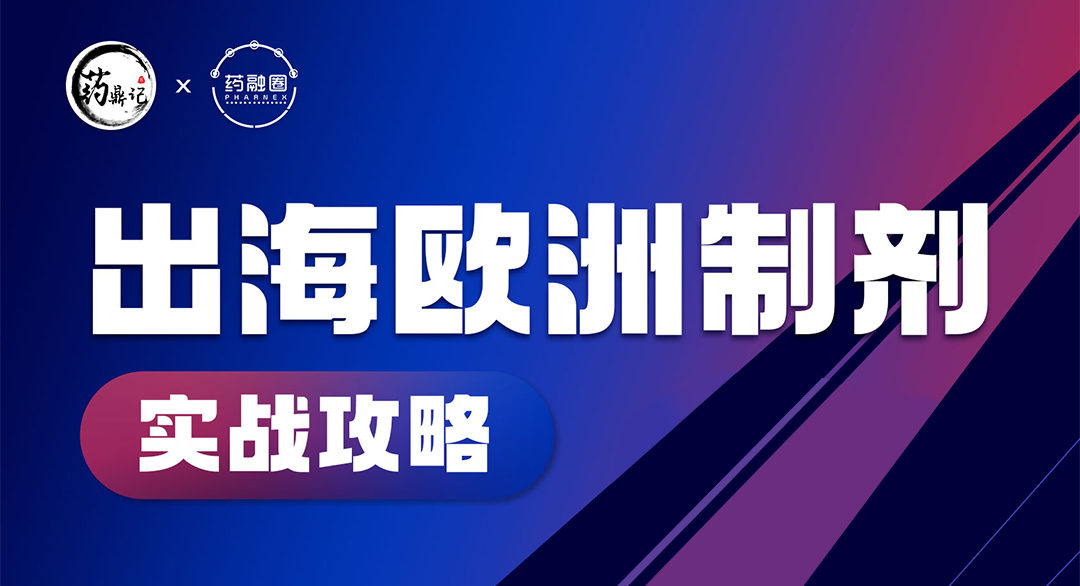 出海欧洲制剂荆士恒制剂出海2054 2024-03-23
出海欧洲制剂荆士恒制剂出海2054 2024-03-23 -
 青蒿素产品契机:探索青蒿素的发现之旅与国际市场机遇许舸、 王悦琳、 王亚峰、 姚立锋青蒿素3231 2024-01-24
青蒿素产品契机:探索青蒿素的发现之旅与国际市场机遇许舸、 王悦琳、 王亚峰、 姚立锋青蒿素3231 2024-01-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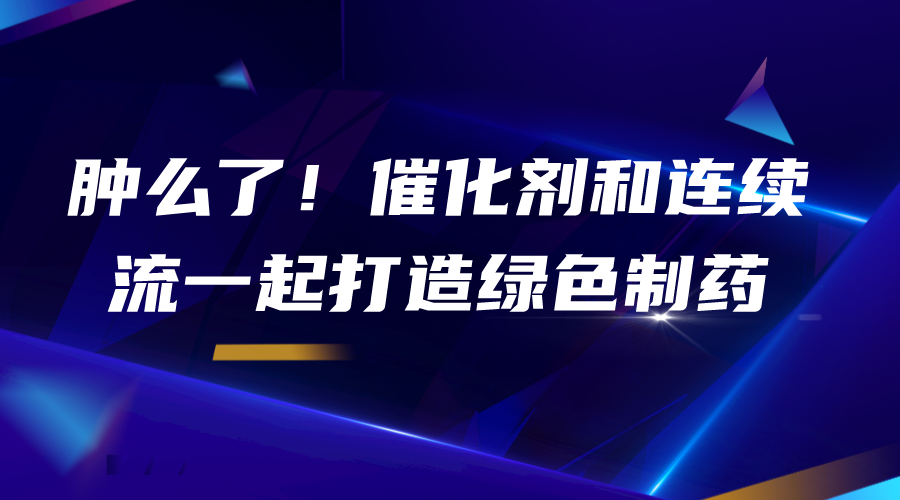 肿么了!催化剂和连续流一起打造绿色制药马兵、 王正、 龙韬连续流 生物催化剂3846 2023-07-31
肿么了!催化剂和连续流一起打造绿色制药马兵、 王正、 龙韬连续流 生物催化剂3846 2023-07-31
-
 眼科产品大起底凌岫泉眼科领域1503 2022-04-04
眼科产品大起底凌岫泉眼科领域1503 2022-04-04 -
 细数眼科领域的临床痛点和潜力项目韩敏眼科领域1543 2022-10-17
细数眼科领域的临床痛点和潜力项目韩敏眼科领域1543 2022-10-17 -
 数说眼科市场冯高雅眼科领域1507 2022-09-26
数说眼科市场冯高雅眼科领域1507 2022-09-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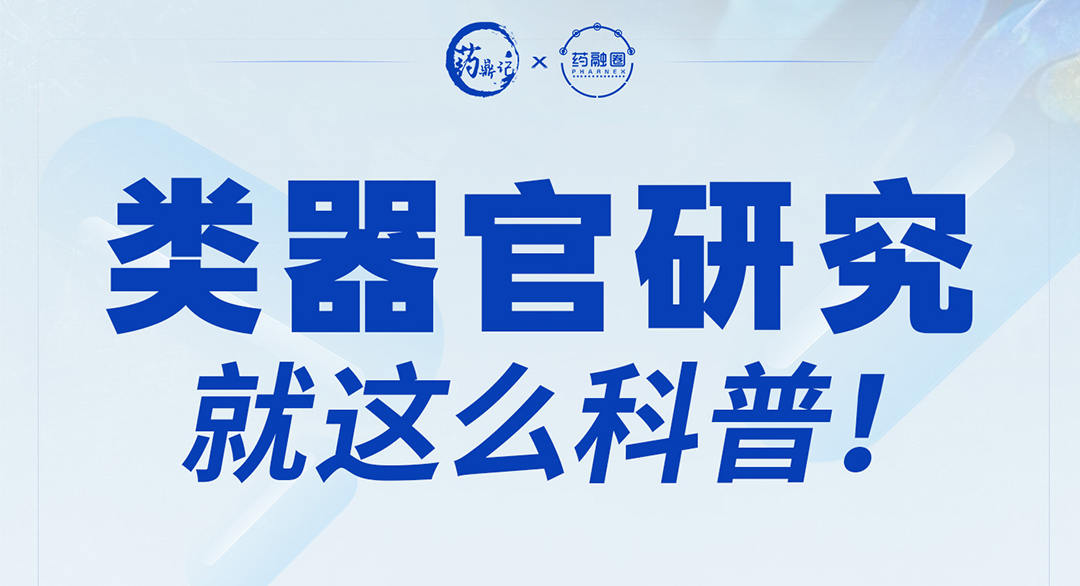 什么是类器官技术?前沿应用与发展方向介绍李长杰类器官2589 2024-05-09
什么是类器官技术?前沿应用与发展方向介绍李长杰类器官2589 2024-05-0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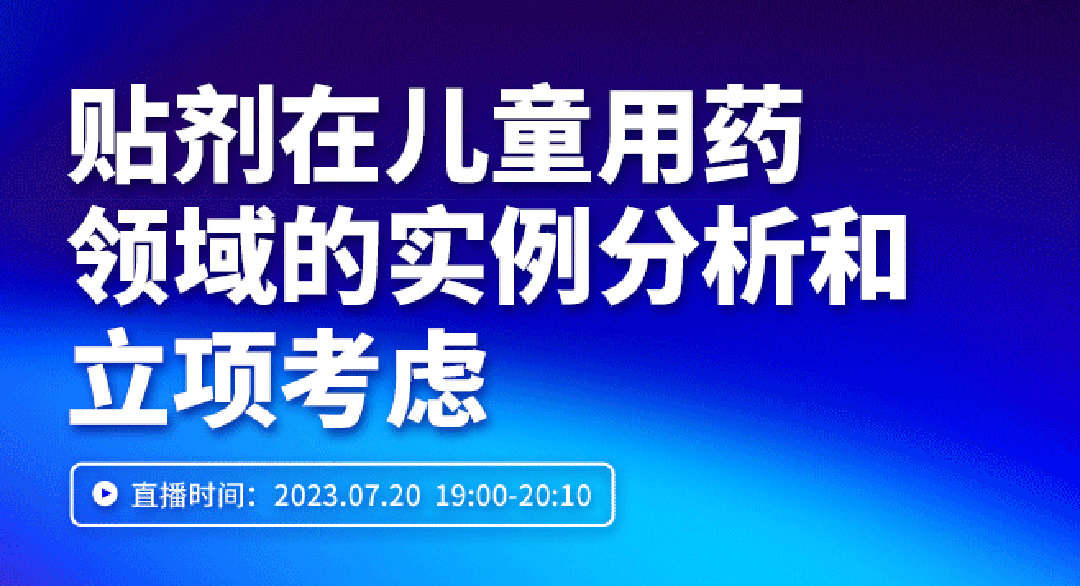 贴剂在儿童用药领域的实例分析和立项考虑吴越、 刘文辉立项 儿童药研发 贴剂3264 2023-07-20
贴剂在儿童用药领域的实例分析和立项考虑吴越、 刘文辉立项 儿童药研发 贴剂3264 2023-07-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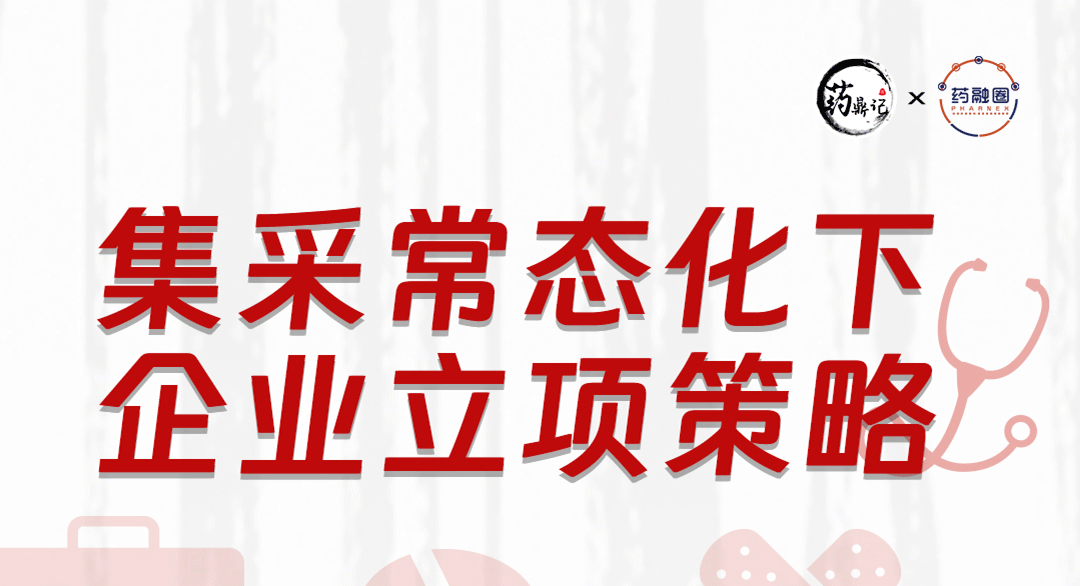 集采常态化下企业立项策略葛志敏集采2389 2023-06-07
集采常态化下企业立项策略葛志敏集采2389 2023-06-07 -
 JAK靶点全景扫描李冉靶点2457 2023-04-03
JAK靶点全景扫描李冉靶点2457 2023-04-03
-
 GPT大模型+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新范示杨成彪、 王文佳、 黄庆春、 吴刚医药行业 GPT大模型1562 2023-05-08
GPT大模型+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新范示杨成彪、 王文佳、 黄庆春、 吴刚医药行业 GPT大模型1562 2023-05-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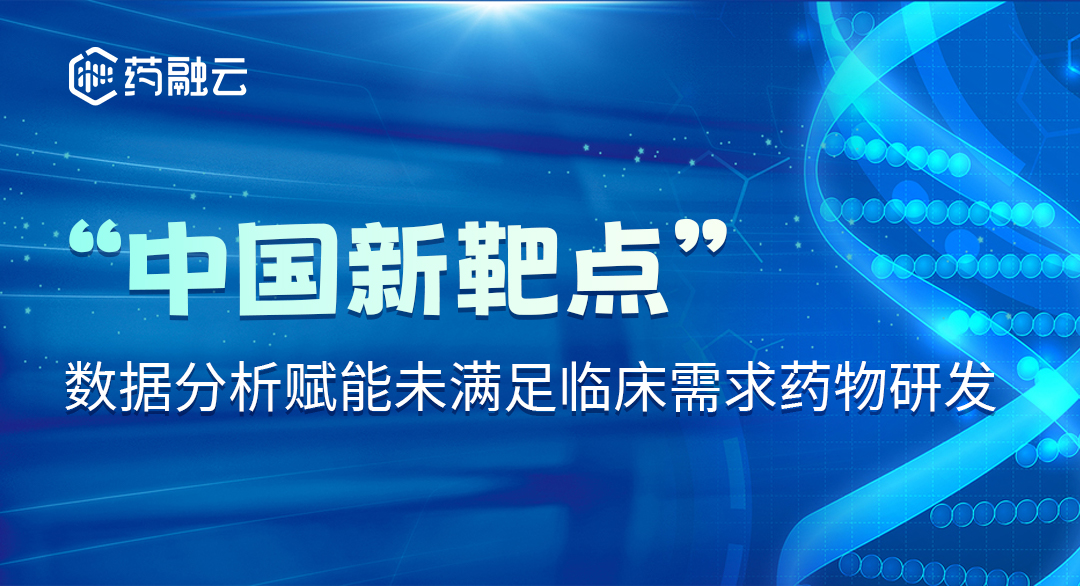 “中国新靶点”—数据分析赋能未满足临床需求药物研发梁崇晟大数据 临床治疗2486 2023-04-10
“中国新靶点”—数据分析赋能未满足临床需求药物研发梁崇晟大数据 临床治疗2486 2023-04-10 -
 中国新靶点—大数据赋能未满足临床需求药物研发徐艺涵靶点 大数据 多靶点创新181 2023-03-06
中国新靶点—大数据赋能未满足临床需求药物研发徐艺涵靶点 大数据 多靶点创新181 2023-03-06 -
 数据+AI高效赋能医药市场营销苏超医药数据库 AI辅助 大数据674 2023-02-06
数据+AI高效赋能医药市场营销苏超医药数据库 AI辅助 大数据674 2023-02-06
-
 医药出海新动向:拉美市场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Julian Oscar Efler拉美市场3654 2024-05-23
医药出海新动向:拉美市场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Julian Oscar Efler拉美市场3654 2024-05-23 -
 抗体产业链发展:深度剖析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及其应用韩蓝青、 查长春、 高新、 滕毓敏抗体产业链 抗体药物开发3250 2024-04-20
抗体产业链发展:深度剖析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及其应用韩蓝青、 查长春、 高新、 滕毓敏抗体产业链 抗体药物开发3250 2024-04-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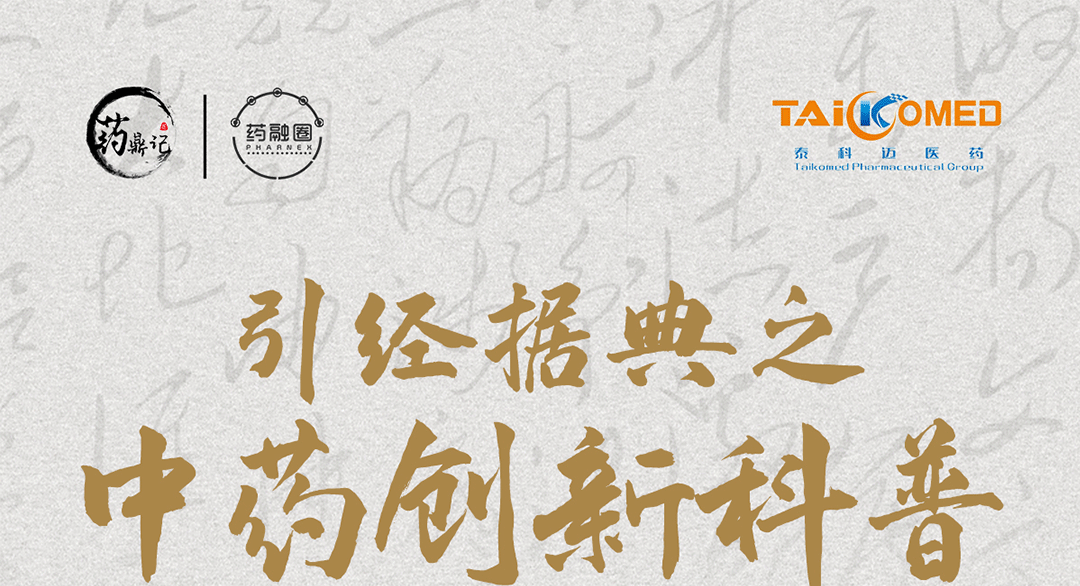 引经据典之中药创新科普唐永红、 徐桂超中药 中药改剂型 中药市场2169 2023-06-06
引经据典之中药创新科普唐永红、 徐桂超中药 中药改剂型 中药市场2169 2023-06-06 -
 合成生物学线上会徐应木、 丁世杰、 相深、 晁然生物学 药物生物 生物医学1457 2023-04-09
合成生物学线上会徐应木、 丁世杰、 相深、 晁然生物学 药物生物 生物医学1457 2023-04-09
药融云端直播
汇聚行业头部资深专家,深度分享前沿干货知识
-
 药物结晶工艺研发重难点分析及案例分享张腾药物结晶工艺3551 2024-04-18
药物结晶工艺研发重难点分析及案例分享张腾药物结晶工艺3551 2024-04-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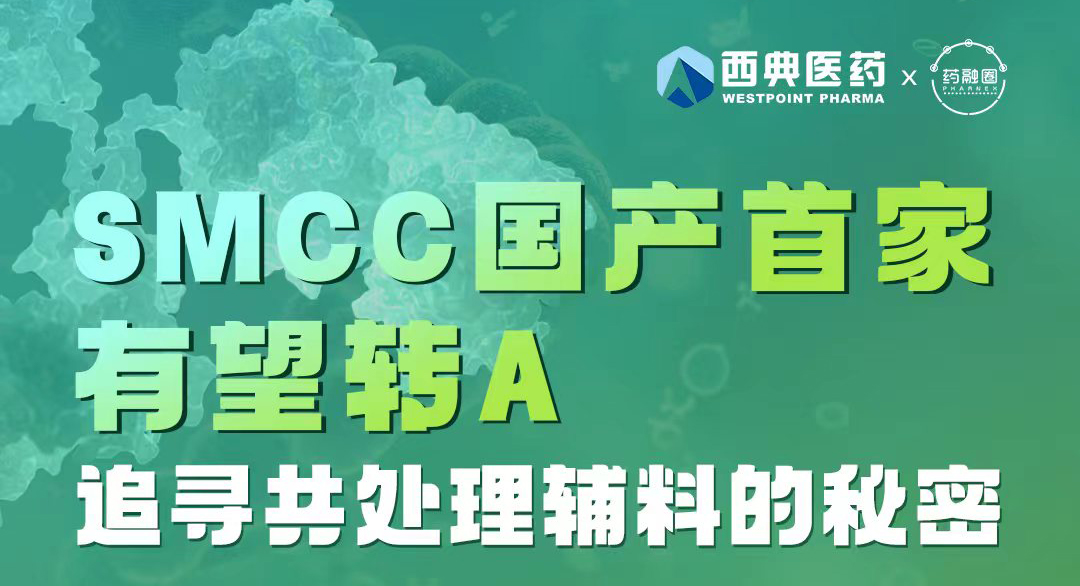 SMCC国产首家有望转A,追寻共处理辅料的秘密郭梦娇药用辅料2211 2024-04-17
SMCC国产首家有望转A,追寻共处理辅料的秘密郭梦娇药用辅料2211 2024-04-17 -
 对话ADC药物研发和质控专家唐宇博、 吴家齐、 申克宇ADC3656 2024-03-27
对话ADC药物研发和质控专家唐宇博、 吴家齐、 申克宇ADC3656 2024-03-27 -
 药物连续流反应制造工艺技术及在线检测手段邓建、 伍辛军、 周影连续流反应3415 2024-03-21
药物连续流反应制造工艺技术及在线检测手段邓建、 伍辛军、 周影连续流反应3415 2024-03-21
-
 药物结晶工艺研发重难点分析及案例分享张腾药物结晶工艺3551 2024-04-18
药物结晶工艺研发重难点分析及案例分享张腾药物结晶工艺3551 2024-04-18 -
 对话ADC药物研发和质控专家唐宇博、 吴家齐、 申克宇ADC3656 2024-03-27
对话ADC药物研发和质控专家唐宇博、 吴家齐、 申克宇ADC3656 2024-03-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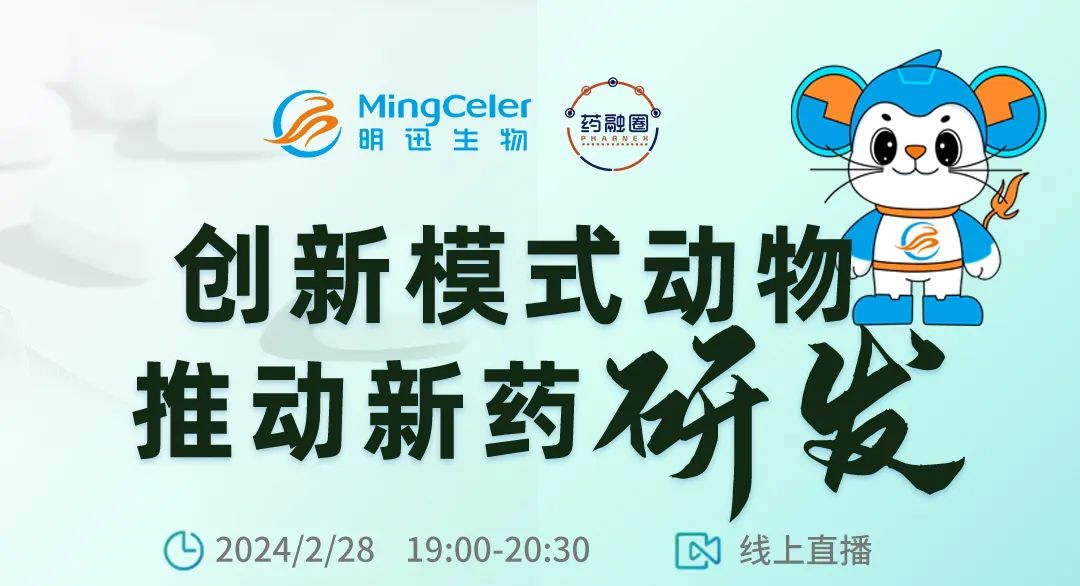 创新模式动物,推动新药研发吴光明、 孙骄杨新药 药物研发1891 2024-02-28
创新模式动物,推动新药研发吴光明、 孙骄杨新药 药物研发1891 2024-02-28 -
 122期:高效且稳定的细胞株开发策略Lena Tholen、 宋佳丽、 王安欣细胞株1552 2023-12-21
122期:高效且稳定的细胞株开发策略Lena Tholen、 宋佳丽、 王安欣细胞株1552 2023-12-21
-
 124期:口溶膜剂型处方工艺和开发应用全丹毅、 潘卫三、 全越口溶膜制剂 工艺开发3285 2024-01-31
124期:口溶膜剂型处方工艺和开发应用全丹毅、 潘卫三、 全越口溶膜制剂 工艺开发3285 2024-01-31 -
 123期:从理论到实践: 缓控释制剂研发指南段云剑、 童伟勤缓释注射制剂5428 2023-12-28
123期:从理论到实践: 缓控释制剂研发指南段云剑、 童伟勤缓释注射制剂5428 2023-12-28 -
 透皮制剂开发要点分析及策略段云剑、 全丹毅透皮制剂7389 2023-11-01
透皮制剂开发要点分析及策略段云剑、 全丹毅透皮制剂7389 2023-11-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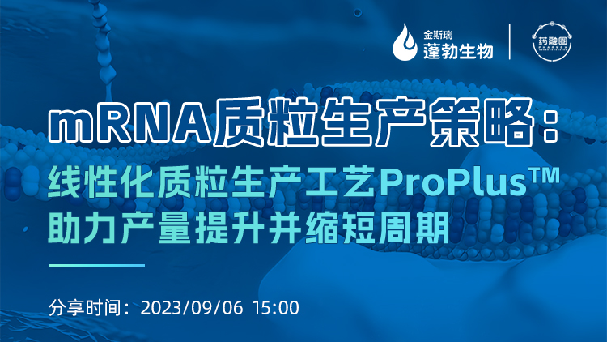 112期:mRNA质粒生产策略:线性化质粒生产工艺ProPlus™倪明mRNA 生产工艺8506 2023-09-06
112期:mRNA质粒生产策略:线性化质粒生产工艺ProPlus™倪明mRNA 生产工艺8506 2023-09-06
药通社
专注医药政策法规、研发技术、立项转化和GXP
-
 雾化吸入液全方位解析:什么是雾化吸入液?雾化器安全性及未来展望常跃兴雾化吸入液2657 2024-06-11
雾化吸入液全方位解析:什么是雾化吸入液?雾化器安全性及未来展望常跃兴雾化吸入液2657 2024-06-11 -
 MAH制度下产品立项与项目管理全解析:质量管理、项目委托与研发生产策略吴军产品立项 MAH制度2629 2024-06-04
MAH制度下产品立项与项目管理全解析:质量管理、项目委托与研发生产策略吴军产品立项 MAH制度2629 2024-06-04 -
 MAH制度引领:如何实现技术转移与工艺管理?吴军MAH制度 技术转移3069 2024-05-28
MAH制度引领:如何实现技术转移与工艺管理?吴军MAH制度 技术转移3069 2024-05-28 -
 MAH制度药品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与GMP实施的特殊性及法规符合性实施途径吴军MAH制度 药品生产管理3265 2024-05-21
MAH制度药品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与GMP实施的特殊性及法规符合性实施途径吴军MAH制度 药品生产管理3265 2024-05-21
-
 雾化吸入液全方位解析:什么是雾化吸入液?雾化器安全性及未来展望常跃兴雾化吸入液2657 2024-06-11
雾化吸入液全方位解析:什么是雾化吸入液?雾化器安全性及未来展望常跃兴雾化吸入液2657 2024-06-11 -
 深入理解定量吸入气雾剂(pMDI)给药技术:pMDI的定义、关键技术及存在的问题常跃兴定量吸入气雾剂3270 2024-05-14
深入理解定量吸入气雾剂(pMDI)给药技术:pMDI的定义、关键技术及存在的问题常跃兴定量吸入气雾剂3270 2024-05-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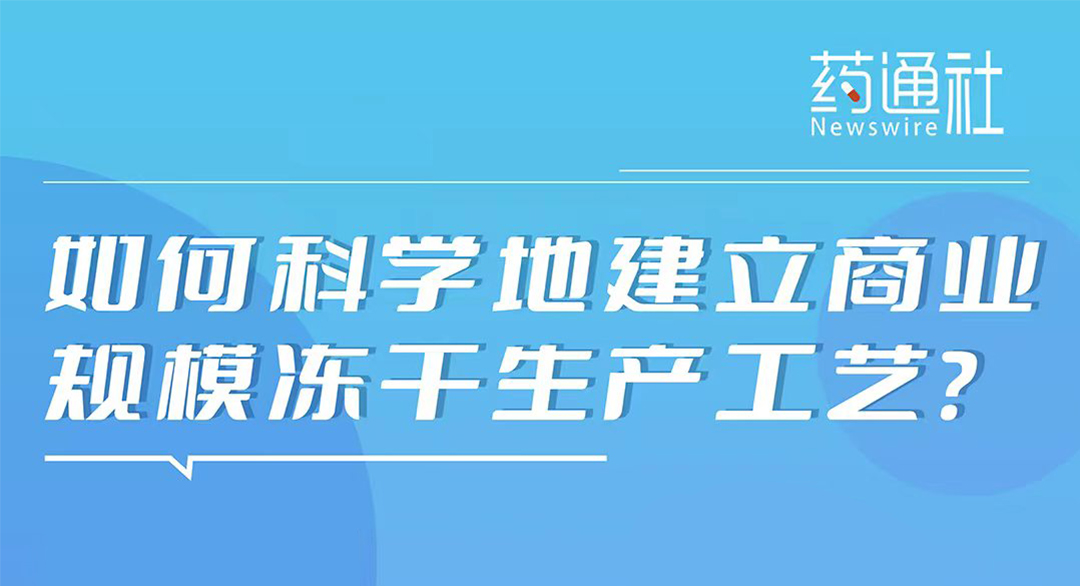 如何科学建立商业规模冻干工艺?关键参数详解与商业化冻干技术转移策略探讨陈建涛冻干工艺3442 2024-04-25
如何科学建立商业规模冻干工艺?关键参数详解与商业化冻干技术转移策略探讨陈建涛冻干工艺3442 2024-04-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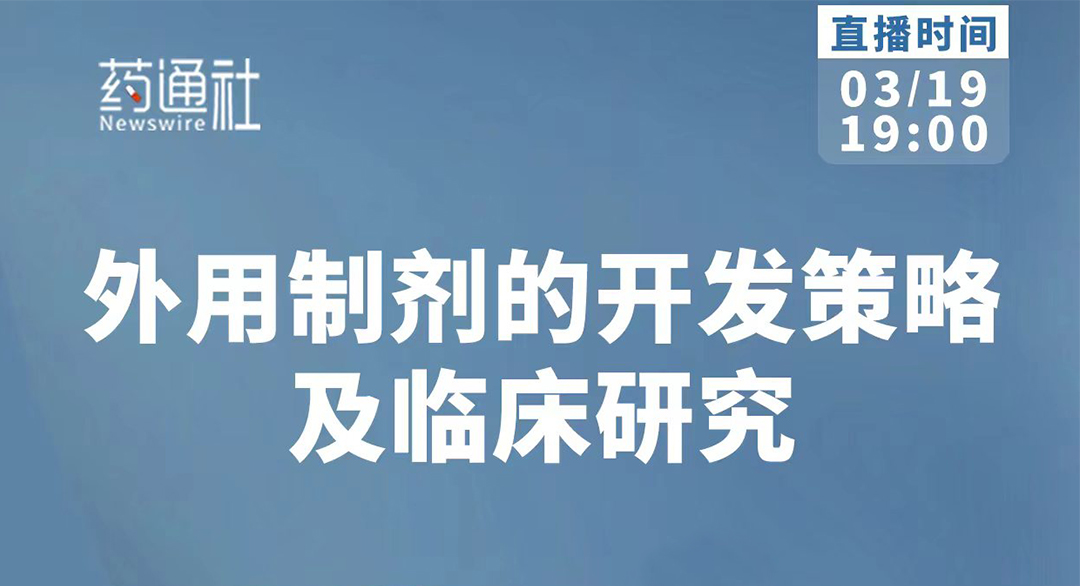 外用制剂讲解:皮肤外用制剂的质量研究策略及外用制剂仿制药临床研究张静、 王欣桐外用制剂3519 2024-03-19
外用制剂讲解:皮肤外用制剂的质量研究策略及外用制剂仿制药临床研究张静、 王欣桐外用制剂3519 2024-03-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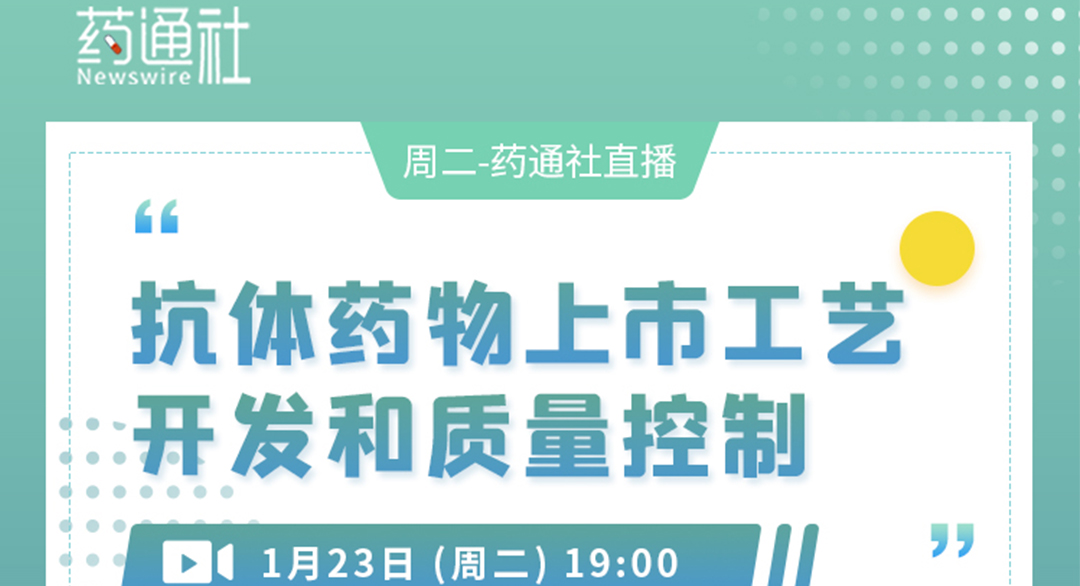 解码抗体药物上市:抗体药物有哪些?上市抗体药物的工艺开发与质量控制策略代虎抗体药物 质量控制 工艺开发2369 2024-01-23
解码抗体药物上市:抗体药物有哪些?上市抗体药物的工艺开发与质量控制策略代虎抗体药物 质量控制 工艺开发2369 2024-01-23 -
 PIC/S系列之数据完整性指南:什么是数据完整性丁恩峰GMP解读 数据完整性2728 2024-01-09
PIC/S系列之数据完整性指南:什么是数据完整性丁恩峰GMP解读 数据完整性2728 2024-01-09 -
 共线风险评估:PIC/S共线评估相关指南、药理独立数据与共线评估流程原则丁恩峰共线风险评估4121 2023-12-19
共线风险评估:PIC/S共线评估相关指南、药理独立数据与共线评估流程原则丁恩峰共线风险评估4121 2023-12-19 -
 PIC/S系列课程07-制药QC实验室检查要点丁恩峰GMP解读 PIC/S系列4647 2023-12-05
PIC/S系列课程07-制药QC实验室检查要点丁恩峰GMP解读 PIC/S系列4647 2023-12-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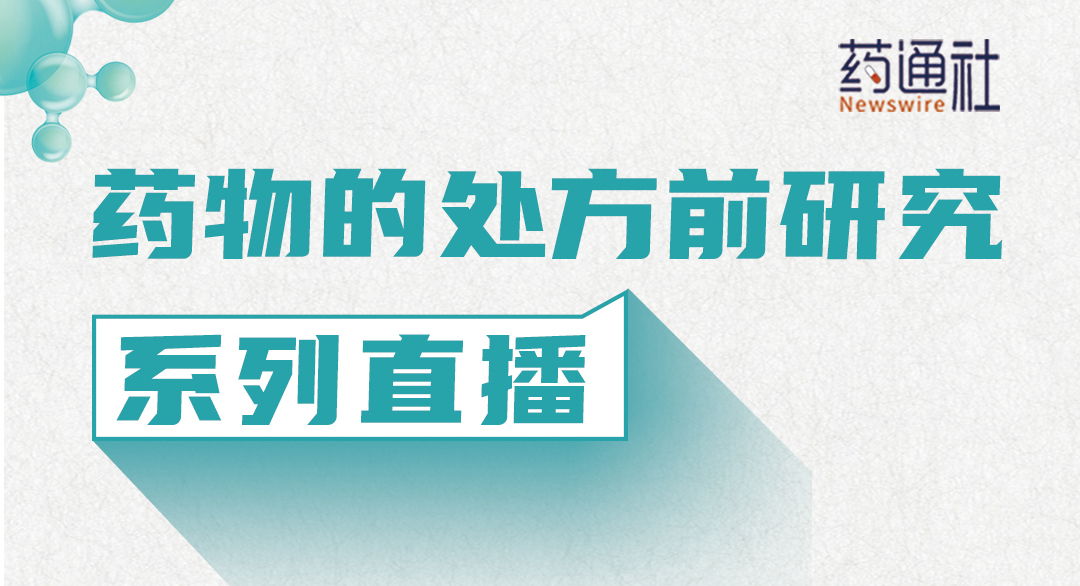 药物的处方前研究系列直播-人体胃肠系统及pH分布刘恒利制剂 药物研发4087 2023-11-07
药物的处方前研究系列直播-人体胃肠系统及pH分布刘恒利制剂 药物研发4087 2023-11-07 -
 ICH M10: 新法规下生物分析研究思路的探讨丁雪生物分析 药政法规2831 2023-08-24
ICH M10: 新法规下生物分析研究思路的探讨丁雪生物分析 药政法规2831 2023-08-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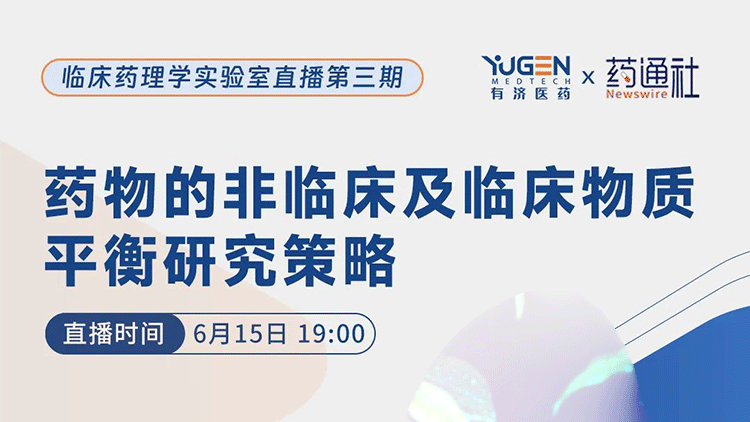 药物的非临床及临床物质平衡研究策略耿雅杰药物分析方法 药物研发3682 2023-06-15
药物的非临床及临床物质平衡研究策略耿雅杰药物分析方法 药物研发3682 2023-06-15 -
 下一站:火热的多肽药物丁伟、 王良友多肽734 2023-04-04
下一站:火热的多肽药物丁伟、 王良友多肽734 2023-04-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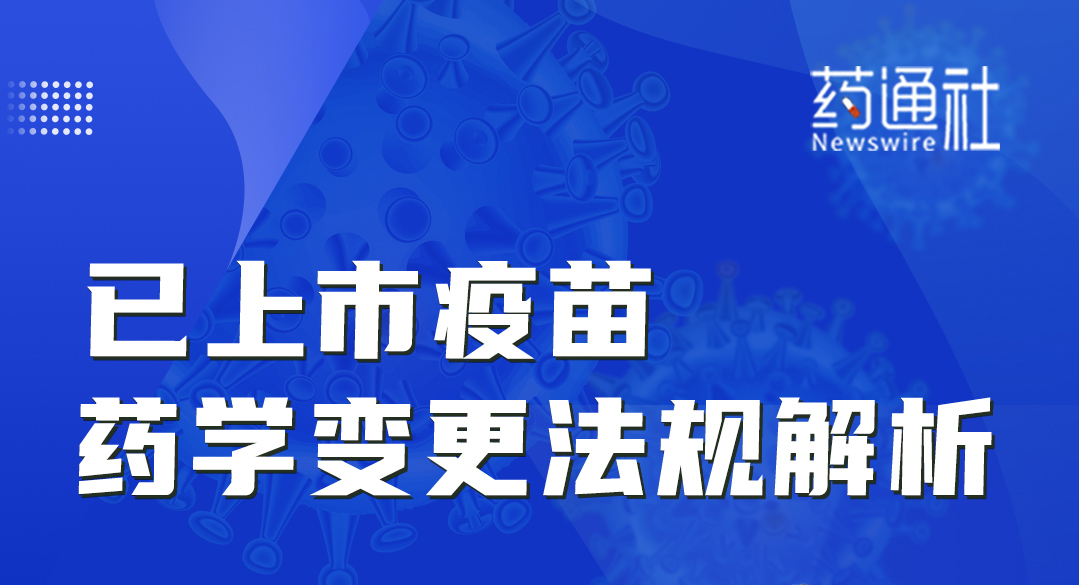 已上市疫苗药学变更法规解析丁恩峰药政法规3467 2023-09-04
已上市疫苗药学变更法规解析丁恩峰药政法规3467 2023-09-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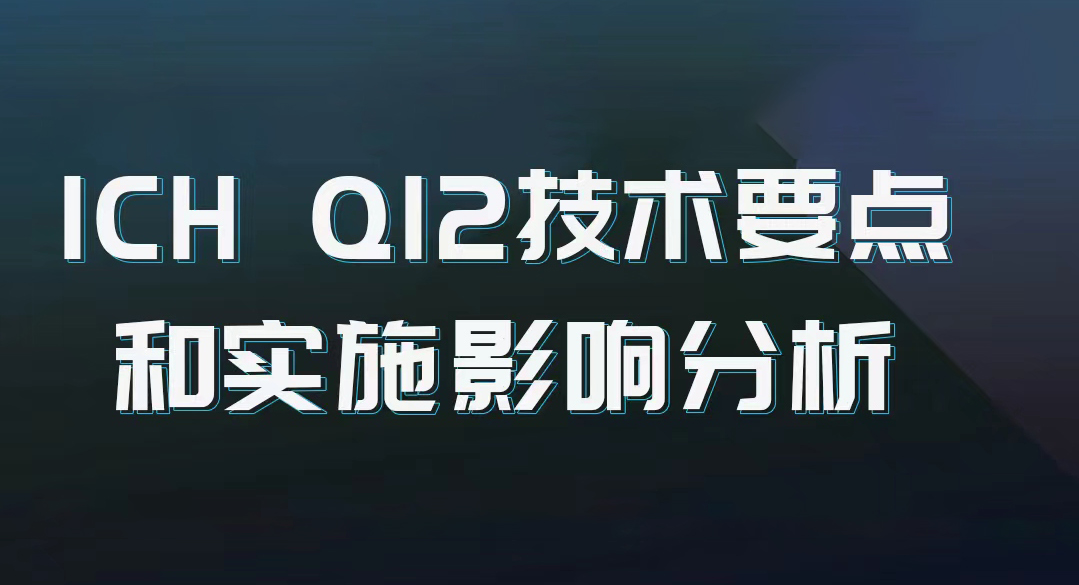 ICH Ql2技术要点和实施影响分析丁恩峰药政法规6867 2023-08-31
ICH Ql2技术要点和实施影响分析丁恩峰药政法规6867 2023-08-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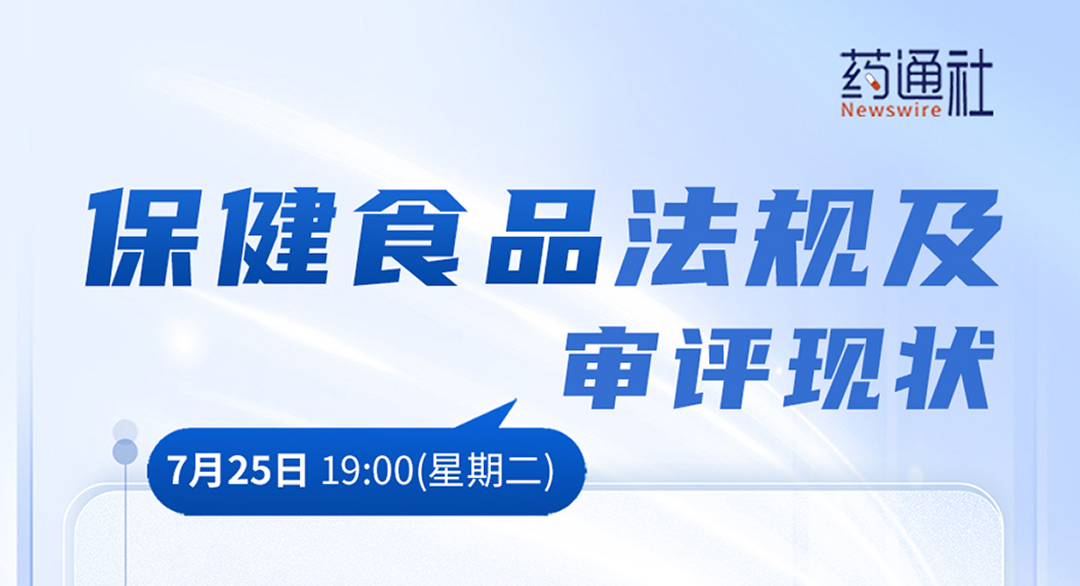 保健食品法规及审评现状刘春燕审评 药政法规3088 2023-07-25
保健食品法规及审评现状刘春燕审评 药政法规3088 2023-07-25 -
 GCP指导原则最新解读和对比丁恩峰药政法规1410 2023-05-31
GCP指导原则最新解读和对比丁恩峰药政法规1410 2023-05-31
-
 MAH制度下产品立项与项目管理全解析:质量管理、项目委托与研发生产策略吴军产品立项 MAH制度2629 2024-06-04
MAH制度下产品立项与项目管理全解析:质量管理、项目委托与研发生产策略吴军产品立项 MAH制度2629 2024-06-04 -
 MAH制度引领:如何实现技术转移与工艺管理?吴军MAH制度 技术转移3069 2024-05-28
MAH制度引领:如何实现技术转移与工艺管理?吴军MAH制度 技术转移3069 2024-05-28 -
 MAH制度药品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与GMP实施的特殊性及法规符合性实施途径吴军MAH制度 药品生产管理3265 2024-05-21
MAH制度药品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与GMP实施的特殊性及法规符合性实施途径吴军MAH制度 药品生产管理3265 2024-05-21 -
 MAH制度讲解之技术转移管理:工艺转移法规、要点及流程丁恩峰MAH制度 技术转移3315 2024-05-07
MAH制度讲解之技术转移管理:工艺转移法规、要点及流程丁恩峰MAH制度 技术转移3315 2024-05-07
-
 解读药物相互作用(DDI):DDI科学研究评估,上市新药DDI总结指导原则李建兰药物相互作用4381 2023-12-14
解读药物相互作用(DDI):DDI科学研究评估,上市新药DDI总结指导原则李建兰药物相互作用4381 2023-12-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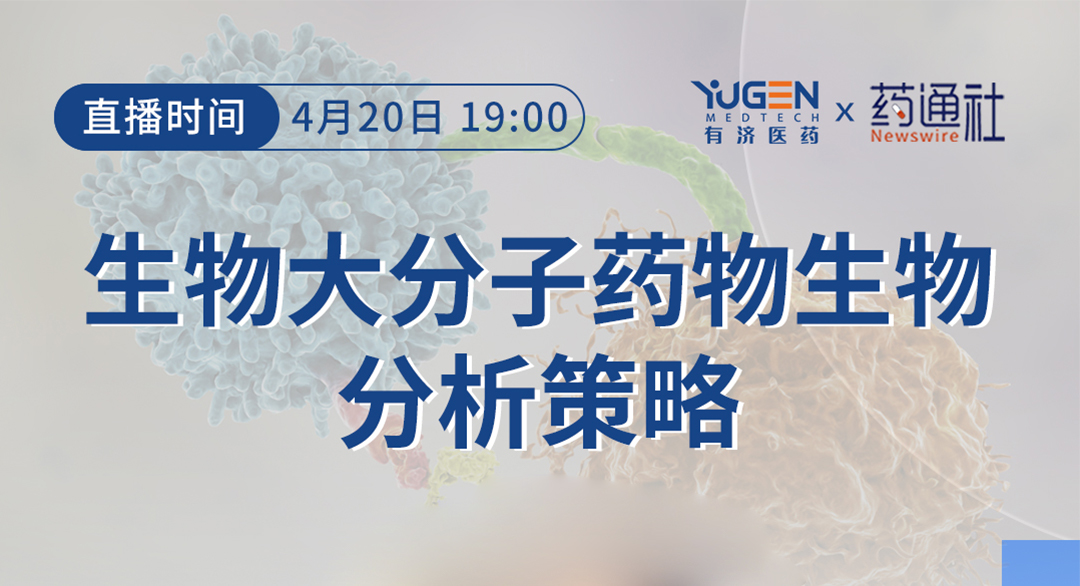 生物大分子药物生物分析策略申文晋大分子 生物分析559 2023-04-20
生物大分子药物生物分析策略申文晋大分子 生物分析559 2023-04-20 -
 生物样本分析经验分享郎士伟生物学 生物样本分析99 2022-12-20
生物样本分析经验分享郎士伟生物学 生物样本分析99 2022-12-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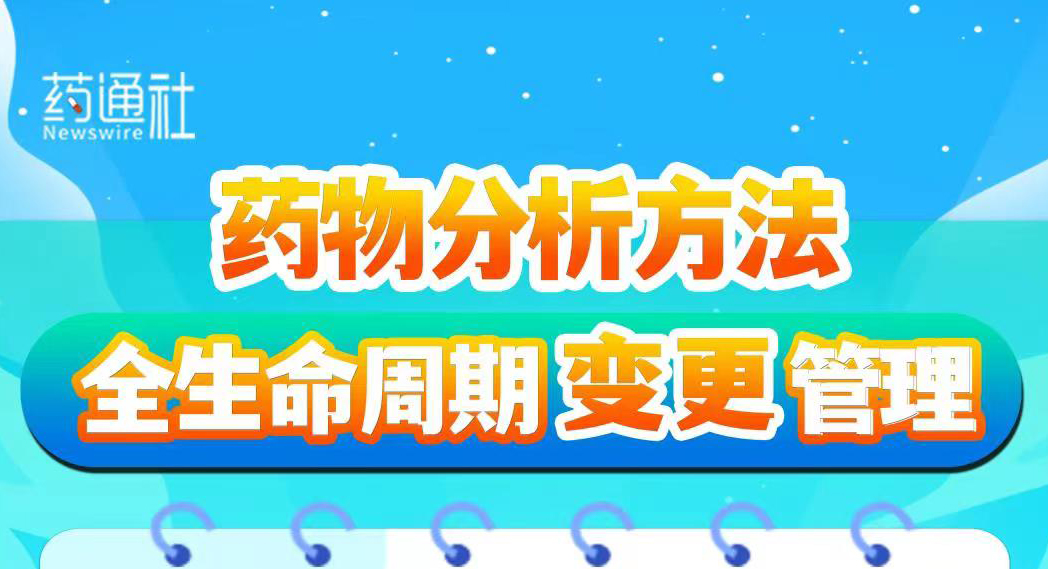 药物分析方法全生命周期变更管理陈洪药物分析方法188 2022-11-29
药物分析方法全生命周期变更管理陈洪药物分析方法188 2022-11-2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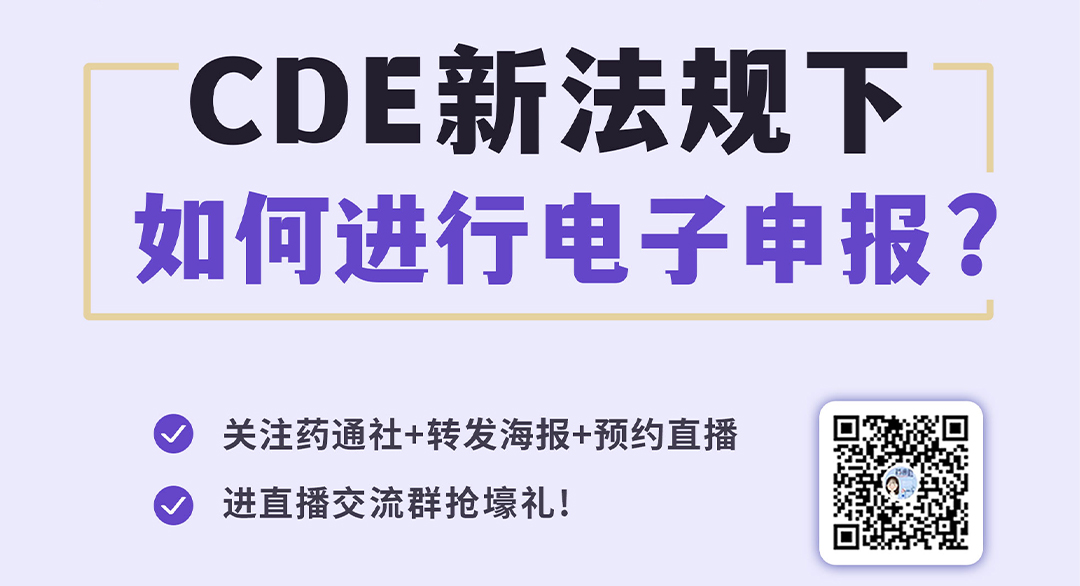 CDE新法规下的电子申报制度学习:电子申报资料制作流程、实操软件及常见问题孔祥敏电子申报制度4312 2024-02-22
CDE新法规下的电子申报制度学习:电子申报资料制作流程、实操软件及常见问题孔祥敏电子申报制度4312 2024-02-2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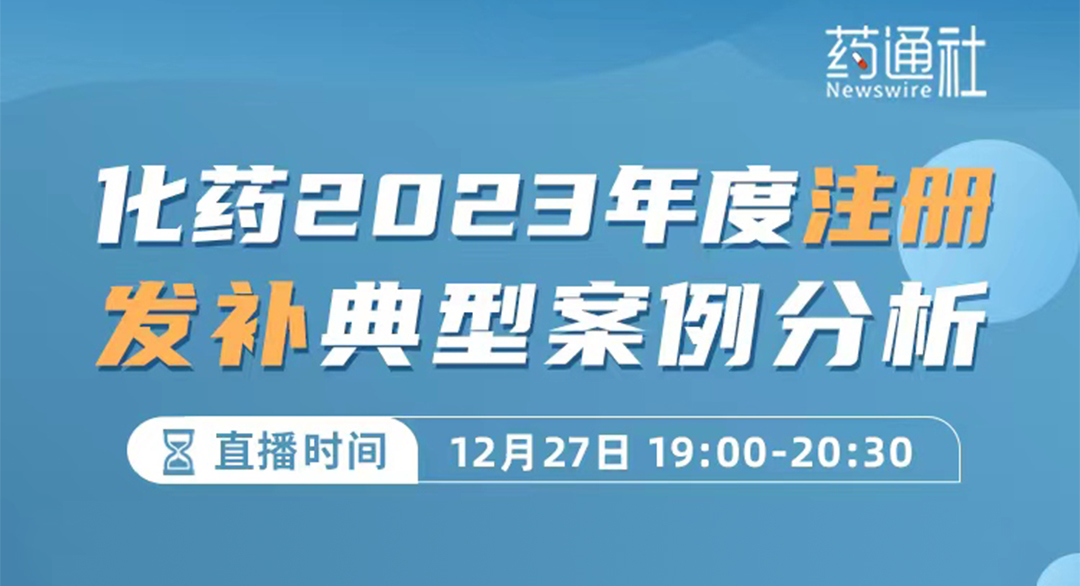 2023年度化药发补案例深度解析:药学发补要求,原料药与制剂的工艺、质量研究发补案例一览丁恩峰注册 药学发补 药典增补4386 2023-12-27
2023年度化药发补案例深度解析:药学发补要求,原料药与制剂的工艺、质量研究发补案例一览丁恩峰注册 药学发补 药典增补4386 2023-12-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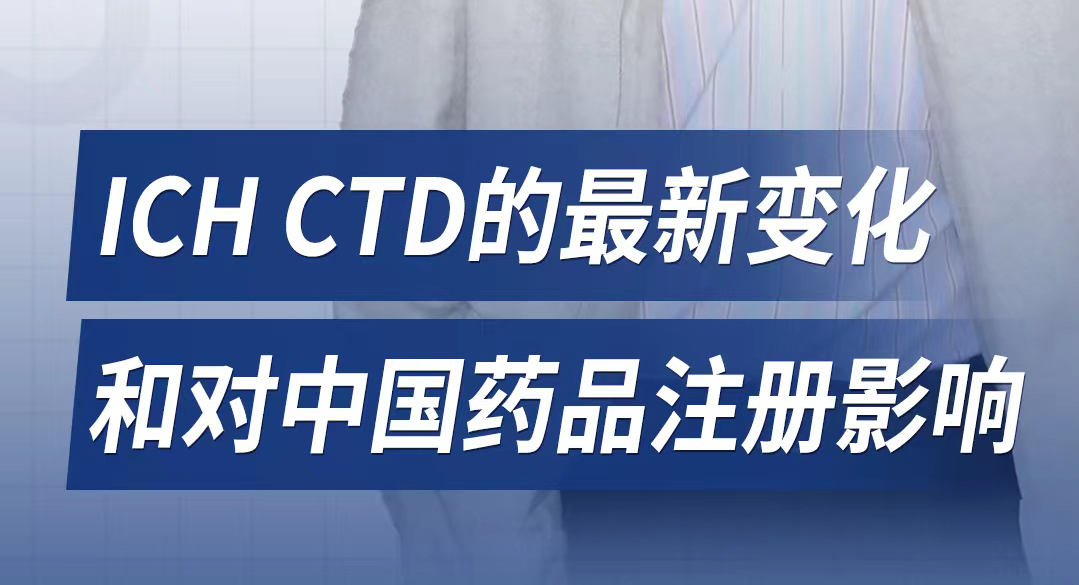 ich CTD的最新变化和对中国药品注册影响丁恩峰药品注册6763 2023-08-22
ich CTD的最新变化和对中国药品注册影响丁恩峰药品注册6763 2023-08-2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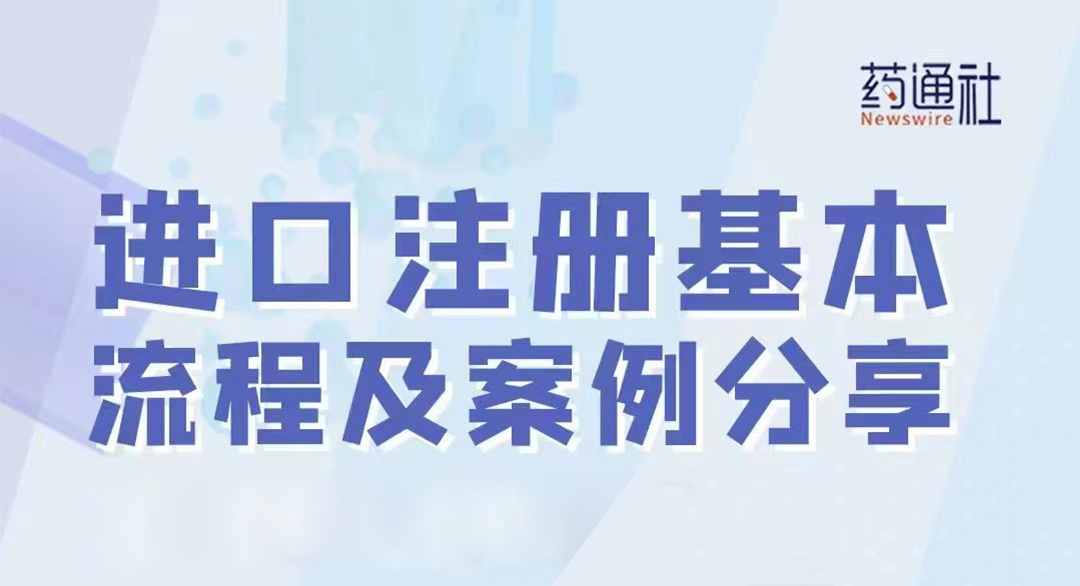 境外生产产品注册基本流程和案例分享刘瑞锦药品注册 注册 欧盟药品注册304 2023-02-21
境外生产产品注册基本流程和案例分享刘瑞锦药品注册 注册 欧盟药品注册304 2023-02-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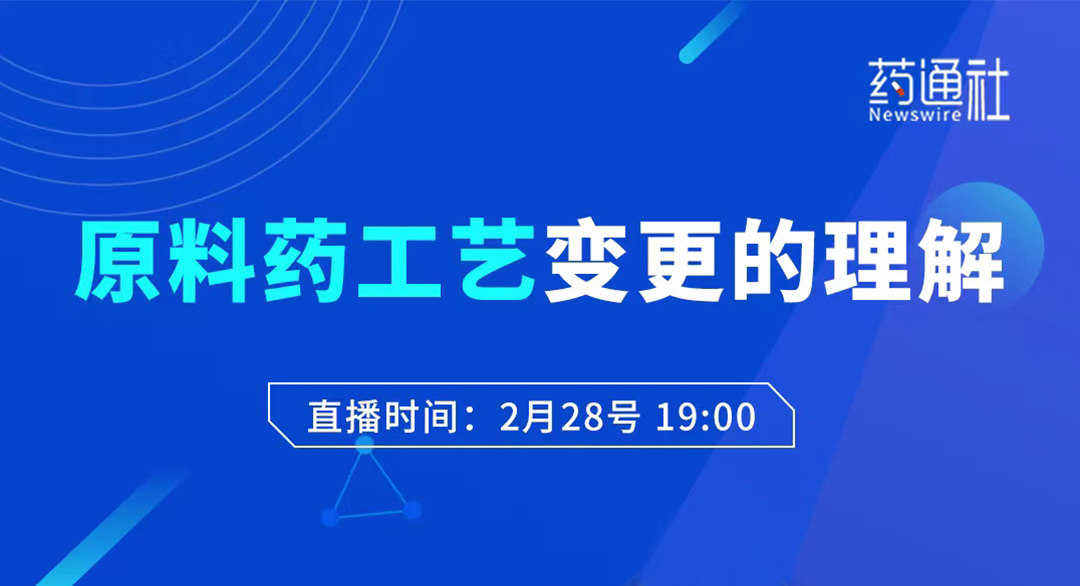 原料药变更讨论及案例分享肖军原料药工艺313 2023-02-28
原料药变更讨论及案例分享肖军原料药工艺313 2023-02-28 -
 原料药美国DMF递交&FDA cGmp检查吴红、 祝传斌原料药 美国DMF149 2022-08-02
原料药美国DMF递交&FDA cGmp检查吴红、 祝传斌原料药 美国DMF149 2022-08-02 -
 原料药登记发补案例分析李银博、 彭贵子原料药293 2022-07-16
原料药登记发补案例分析李银博、 彭贵子原料药293 2022-07-16
-
 无菌企业CCS建立流程和要点丁恩峰无菌企业3335 2023-05-30
无菌企业CCS建立流程和要点丁恩峰无菌企业3335 2023-05-30 -
 BFS生产线设计与管理陈衡山、 李建德、 张孝君生产评估 共线生产101 2023-02-14
BFS生产线设计与管理陈衡山、 李建德、 张孝君生产评估 共线生产101 2023-02-14 -
 共线生产评估策略及案例分享李春艳、 李宏业生产评估 共线生产854 2022-11-15
共线生产评估策略及案例分享李春艳、 李宏业生产评估 共线生产854 2022-11-15
-
 仿制药立项思考:仿制药如何立项,明确立项方向罗刚仿制药立项3907 2024-01-02
仿制药立项思考:仿制药如何立项,明确立项方向罗刚仿制药立项3907 2024-01-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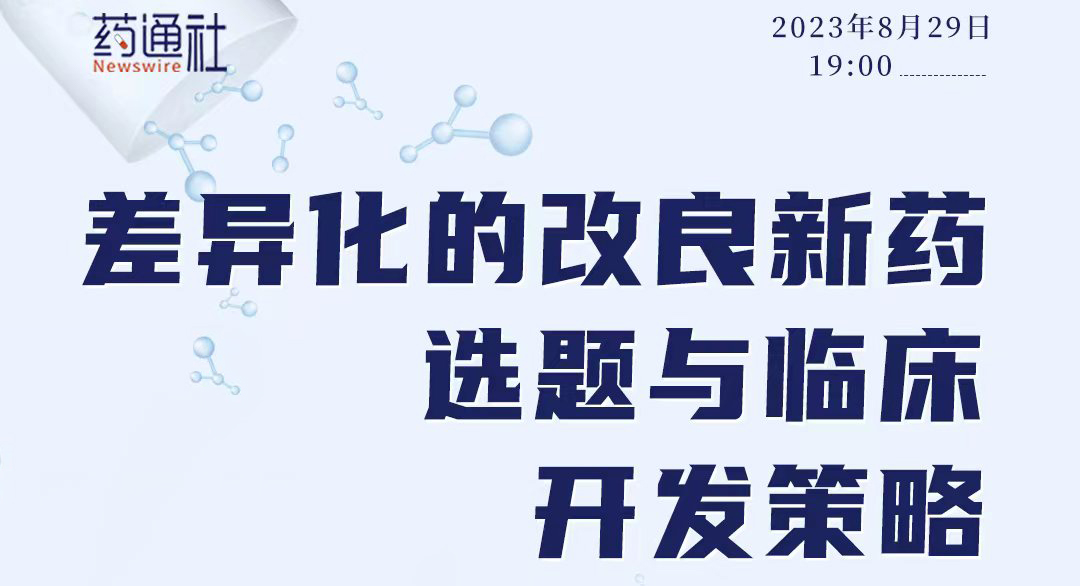 差异化的改良新药选题与临床开发策略夏燕改良新药 差异化策略 临床开发策略5860 2023-08-29
差异化的改良新药选题与临床开发策略夏燕改良新药 差异化策略 临床开发策略5860 2023-08-29 -
 改良新药立项决策王立峰立项 改良新药7005 2023-08-01
改良新药立项决策王立峰立项 改良新药7005 2023-08-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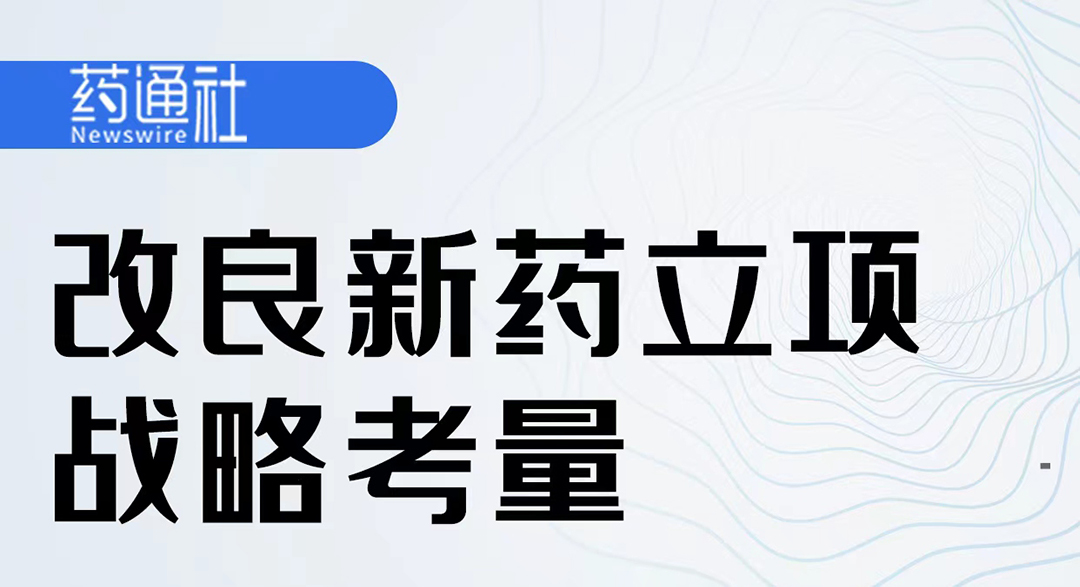 改良新药立项战略考量魏利军药物立项 药企战略 改良新药6528 2023-07-27
改良新药立项战略考量魏利军药物立项 药企战略 改良新药6528 2023-07-27
Q&A知识
来自医药界顶级大咖一对一解答
什么是“合成致死”?在该策略的布局中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樊后兴创始人,CEO
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PARP抑制剂,它主要是针对BRCA突变这一类肿瘤,特别在一些妇科肿瘤里比较常见,包括胰腺癌也获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首先上市的是阿斯利康的奥拉帕尼现在全球销售额已经突破30亿美金。
最近几年,“合成致死”由PARP抑制剂也扩展到其他的一些靶点。属于第二梯队的一些靶点,比如ATR、Wee1、DNA-PK等等,包括PRMT5,国内外研究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公司也在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公司,他们可能会采用高通量的基因敲除,包括利用组学的数据去分析找一些新的靶点做。
“合成致死”的概念最开始是从生物里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两个非致死的基因,如果同时敲除的话,它可能会导致细胞的死亡或者发育的障碍,但是你如果单独地敲除一个细胞对它的生长没有影响的。所以它相当是要一个配对才能发生,那么在肿瘤的治疗里,它的意义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一些靶向药的治疗,大概就是针对致癌基因的疗法,针对这个致病的蛋白来抑制这个蛋白的功能。
比如TP53这些转录因子,它的功能是发挥抑癌的作用,我们从小分子的角度上,像TP5这样的转录因子,它的表面非常光滑,你很难用小分子激动它,即发挥它的功能。但是对于抑癌基因的突变,你能不能找出它的一个搭档?我不直接针对TP53,我干预它的搭档,抑制搭档的功能,达到抑制TP53突变肿瘤的效果,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同诺康在“合成致死”靶点这方面的布局考虑。首先我们联合创始人是同济大学的刘琦教授,他主要是做人工智能跟多组学的,“合成致死”就是针对基因两两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针对组学的分析,包括加入人工智能的算法,这个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首先是靶点发现的问题,我们也构建了一个知识图谱的平台,把所有“合成致死”的靶点,包括肿瘤的数据形成一个抑制的网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根据已知“合成致死”的靶点,就是已知的两个基因之间的配对去预测一些新的“合成致死”的配对,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靶点,当然包括老药新用,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里已经整合了药物跟肿瘤,像这三者数据,我们可以找一些老药新用的机会,包括联合给药的机会。
另外肿瘤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另外搭建了一个多维度前景评估的平台。我们希望在多个维度数据的情况下评估肿瘤的靶点,我们结合了一些单细胞测序的数据,包括临床病人组学的数据,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评估每个适应里面不同“合成致死”的靶点,并且对每个靶点进行打分以及结合临床上的一些数据,包括病人的预后的数据,所以就可以做到在立项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参考。
第三个方面就是AI在临床方面的应用,AI跟多组学的一些数据,包括临床病人组学的数据,以及高通量基因敲除的数据,再加组学数据的分析,其实这个适合找一些针对我们某个“合成致死”靶点的药物,它到底适合哪些病人?这个是可以找一些标志物,我们现在这一块做得少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在正式推临床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做这样的工作。
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搭建其他的平台,比如根据临床病人组学的数据,怎么找靶点,找致病的驱动基因,在找到驱动基因的情况下,我们再找主要的致病驱动基因它的“合成致死”靶点,从而干预它,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在搭相关的一些平台。
分子设计的平台,我们也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跟组学的数据结合起来,因为“合成致死”本来就是基因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更多的是根据组学的数据来的,这就是我们在“合成致死”方面的考虑。另外就是对于靶点来说,我们会做更新的靶点,瞄准现在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些肿瘤,就是靶向治疗跟免疫治疗没有很好解决方案的一些肿瘤,所以我们的主要精力在“合成致死”,我们布局了四个管线,其中最快的一个管线已经确定了PCC主要针对TP53突变的肿瘤,TP53也是实体瘤里非常常见的肿瘤,大概占到40%以上的突变。我们这个靶点国外有一家公司已经推到了临床一期,我们在临床前的药效数据跟他比,在停药以后我们可以持续地抑制肿瘤,肿瘤不反弹,所以我们也是在筹划正式的临床前研究,尽快进行IND申报。包括我们在“合成致死”也布局了其他三个靶点,有两个靶点做得比较快,有一个靶点我们已经做的动物实验有比较好的效果,另外一个靶点即将进入动物实验阶段,这是我们大概在“合成致死”方面的布局情况。
2024-04-19
60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新药分享:作用机制和脱发副作用情况是怎样的?
娄实联合创始人
对于做药人来说,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由于经血倒流进入到子宫之外,着床,产生感染,产生疼痛。子宫内膜本来是在子宫内部,产生周期性脱落,它会随经血排出体外,如果它跑到输卵管或者其他子宫之外的部位,那就会导致炎症的发生。随着各种激素周期性的影响都会刺激它,在月经来潮的时候发生疼痛,疼痛多半是轻度、中重度,一旦发生中重度以上可能就需要休息,当女性荷尔蒙的各种激素恢复到一定水平,它就会缓解,实际上这是针对女性荷尔蒙分泌导致的问题,但是这些荷尔蒙的分泌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在现有的疗法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假性的避孕或者是荷尔蒙截断让患者出现假性绝经的状态,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降到最低,当然也就不来月经了,也就没有周期性疼痛,但是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假性绝经所产生的副作用,像潮红、偏头痛、骨质疏松、更严重的还会产生抑郁和自杀倾向等等。
当我们用现在这种疗法都是可以把它彻底回避的,也就是我们不以减少雌激素的分泌为目的,我们只是对泌乳素的受体给它这个通道加了一个开关,所以它完全不影响其他雌激素的分泌,所以由雌激素降低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没有了。同时很多患病女性都是在育龄期,而恰恰这些女性在生育有很大的需求,在服用其他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也就是在绝经的状态下它们是不可能怀孕的。我们这个药的治疗将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的生育需求带来很大的可能性,虽然现在还没有临床数据来测试,但是从原理的分析上它能够带来这样的获益。
针对脱发我们在临床前动物动物身上做了非常严谨的研究,直接数据告诉我们只是在脱发严重的区域,它会出现生发的状态。,而在不脱发的区域基本上是在百分之十几的范围之内波动,基本上从统计学上来讲,它基本上等于没有副作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毛发的多少是由毛囊来决定的,只有那些已经处于脱发或者睡眠状态的毛囊,你去刺激它的时候,它才会有复苏的可能,好好的毛囊,你再怎么刺激它都不会过度地生长。这样的逻辑就很好地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一些生理的状态、激素水平出现不正常的时候,你要把它调回来。我觉得这有点像当年陈列平教授讲的,你要有一个正常的PD-1的水平,才能保持一个微环境的正常状态。就是在激素水平太高太低都不行,保持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的时候,由激素水平不正常导致的这些疾病就会被克制。
在动物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它治疗脱发,而且在停药以后,我们在两年、三年、四年都看到当时生长出来的头发还继续存在,至于这样的效果能不能在人身上得到复现,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考量我们给到患者身上顶多才有一年的时间,可能需要有更长的时间观察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看到的数据都是支持这个方向的,它不会发生像米诺地尔,你给药的时候它会有生发的效果,停药以后就立刻反弹,这样就导致实践当中能不能停止用药。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系统给抗体药两周一次,能够在一个疗程,不管是六个月还是以后停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的毛发生长能够保持,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两年,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局部用药,你涂它就生发,你不涂就没有。
关于价格方面,一个抗体药,无论你再怎样去生产,做出来它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昂贵的生物药,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对标的是更多的是现在的植发。在米诺地尔、非那雄胺广泛使用,但是不能满足患者需求的情况下,只能靠手术移植的方案,但是很多植发的人都不想植第二次,所以大家对我们这个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2024-04-19
5
如何应对肿瘤患者消瘦适应症?全球针对GDF 15和GFRAL的研发现状如何?
王春河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
人的代谢其实有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是GDF 15,还有一个是GFRAL。GDF 15是肿瘤细胞会高表达,GFRAL主要表达在脑垂体里面,当GDF 15跟GFRAL结合之后,就把整个代谢改变了。一方面它会减少进食,使得人没有食欲,即使吃进去,消化了,但是它不能够转化成人体的脂肪,还有蛋白,另外它会把人体现有的脂肪跟蛋白分解掉,分解掉使它排除体外,所以会消瘦。
其实GDF 15蛋白本身是可以减肥的,但是有些病人会忧虑太瘦,像晚期的肿瘤病人,过度节食导致的厌食症、神经性呕吐,还有天生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等等其实这些人都是需要增加它的同化功能,使他可以更多的地摄入营养,营养摄入之后能够更好地被利用,我们这个品种是阻断的GDF 15与GFRAL的结合,我们做的是一个GFRAL的抗体。
当前国外走得最快就是NGM Bio公司,他们在1B期的时候,在晚期的胰腺癌里面看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这个效果一方面是包括肿瘤病人体重的下降被逆转,另外就是实实在在地看到肿瘤组织的缩小,所以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惊艳的,所以他现在也进入了二期的研究。
在国外来讲,其实做靶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NGM,还有辉瑞,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做的GDF 15抗体,这两个一个是配体,一个是抗体,其实做哪个我觉得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们看到的是GFRAL的数据非常好。辉瑞现在针对GDF 15,这个品种,也进入了临床二期,当时他发了个简报说1B期的结果是积极的,但是我们没看到他的效果,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没底的,我们就做了GFRAL抗体。
国内的话,石药他们获得了一个IND,现在正在做临床一期,我们是比他们稍微慢了一点。那么我们现在报了Pre IND,可能比他们实施晚了几个月。国内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公司在做这个品种。
2024-04-19
0
如何借助FDA经验和AI技术,实现临床推进的高效路径?
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多的时候有五六位是从FDA出来的,其实是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把五个IND都已经申报上了,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我们来自于FDA,对FDA的审评,对他的这些途径,对他的要求这方面我们理解的程度可能比一般的新创公司要更全面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在应用上,我们早一点是用505b(2)的方式来做新药,我们选择的开发难度和开发的时间都比较适合于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充分应用了我们的技术专长和技术背景。结合这两点,我们才能做出5个IND,还不在印度和拉美国家做的。
另外从临床操作上,我们拿到IND后,就把第一个临床试验推进下去,大概4个多月就把一期临床试验做出来了,其他的二期、三期我们也有的在做,有的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能做的尽快把他做起来,同时后期比较花钱的临床二期、三期,我们也会掌握进度,所以我们在控制速度,优化管线安排上应该算做的比较不错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AI我们用到哪些地方?我们的AI并不像传统的AI,我们没有花功夫在分子设计、分子筛选上面,我们是用到临床上,在临床上应用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临床设计,一个就是新靶点的筛选,特别是新靶点的筛选,这个需要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对靶点、通路的理解,你光靠人的认知或者运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AI在这些方面能够帮助到我们,在筛选品种上的确是有帮助的,包括筛选以后验证我们的筛选是不是对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AI能在临床试验的设计(Clinical Trial Design),包括临床操作方面帮助我们,其实AI在用到我们自己的产品之外,我们现在也会做一些服务方面的工作,我们建立了自己的AI软件,还有数据库,对于我们40多人的公司,这个产能是超过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用以外,我们也在帮助有需要的企业或者机构。
针对癌痛与晚期肿瘤消瘦的药物创新:解析一家公司的差异化立项策略
我们主要瞄准的是肿瘤病人的并发症,一方面就是癌症病人的疼痛,其实疼痛是癌症病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后期的癌症病人基本上是个个都疼的,现在一些肿瘤药、靶向药,还有免疫调节的药都是以延长病人的寿命为目标的。现在很少有药着重于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我觉得生活质量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第一个药就是针对癌症病人疼痛的,靶向神经生长因子(NGF)
最早做这个靶点的其实是辉瑞,当时他就选择了两个适应症,一个是骨关节炎,另外一个就是慢性下腰痛,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比如在骨关节炎里,它的药效其实比现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奥施康定的效果还是要好的。在慢性下腰痛里,它也跟曲马多进行对比,发现它的药效其实也强于曲马多的,既然有这么好的药效,那为什么它没有上到临床呢?主要就是发现他会造成个别病人关节炎进展的加速,因为在慢性病里,其实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药效,而且发现随着用药周期的变长,关节炎加速的比例也会增加,那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非常长期的用药的时候,这个比例会不会变得非常惊人不可接受,这个时候辉瑞是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药在申请骨关节适应症上市的时候,它就被毙掉了。
我们就是看到它药效不错,这个药在关节炎里不行,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适应症?那我们觉得非常好的适应症就是癌痛,因为癌痛有两点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用这个药,第一点就是他没有长期用药的需求,因为癌症病人可能过个一年半载,他已经不在了,在这类病人中主要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另外就是这些病人基本上是不动的,他得了癌症,他不可能再去打羽毛球或者是自己登山、跑步这些事情,所以也就避免了这个药,在骨关节炎里出现关节炎进一步加快的问题。
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觉得这个药用癌痛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一旦成药之后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因为吗啡这类阿片类药物耐药之后,病人的痛苦是没办法得到解决的。特别是我们国家的阿片类药物的用量是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如果我们这个药做成之后,就有可能是全球第一个给饱受癌痛困扰的病人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基于这个主线,我们还有两个品种是针对晚期肿瘤病人消瘦。
因为我们知道晚期的癌症病人都特别的瘦,当特别瘦的时候,其实更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免疫力会很低下。我们知道免疫反应是极度需要能量的,我们的免疫细胞会快速地扩增,这个扩增需要大量的能量,如果没有一个能量的支持,免疫系统的激活其实是不可能充分的,你再用PD-1这些抗体激活它是没有用的,所以改善这类病人的营养状况其实非常重要的,但只是增加营养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肿瘤细胞会分泌大量的GDF15,GDF 15跟它的受体GFRAL结合之后,就把它的同化作用给大大的减弱了,而把它的异化作用给激活了,导致他的食欲不振,这些病人没办法通过补充营养的方式来克服过度消瘦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了这样一个抗体。国际上也有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做了一个类似的抗体,他们在胰腺癌里发现就是这个还是非常有效的,能够促进晚期的胰腺癌病人体重恢复,通过增加他的营养恢复它的免疫力达到了肿瘤缩小的效果。我们这个药是一个快速跟随的项目,通过治疗肿瘤病人的并发症,真正地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使病人的生命不管是长度还是宽度得到拓宽,我觉得对病人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医药公司创业故事分享: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主旨是做创新药的,但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新公司,如何生存到10年,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在国内做创新药研发,基本上是找不到融资的,这个是在战略选择上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公司可能跟大部分中国新药研发公司不一样,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如何创造自己的造血能力,我们公司现在的战略是两句话,叫做仿制助力创新、创新驱动未来,也就是我们公司是仿制药、创新药两条腿一起走的。
其实仿制药从2016年国家药政改革到现在一系列的药政改革,其实有非常大的机遇。我觉得我们公司实际上是在仿制药层面抓住了这个机遇。主要有几个政策,一个是MAH制度,另外一个就是仿制药的一次性评价,接下来是国家药品集采这三大关键点。
利用仿制药这条腿,在2020年我们有了第一个仿制药批文上市,接着马上就赶上集采,所以我们到2021年的时候第一次实现了盈利,2021到2023年我们是连续3年实现盈利,这应该算是我们公司第一层次的发展。其实仿制药这条腿的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它给了我们创新药研发比较有底气的现金流,让我们新药研发团队非常有底气,不管我们的创新药项目遭遇什么困难甚至失败,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生存。
对于创新药,我们觉得如果要创新药一定要有差异化,一定要抢美国市场,这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确实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是做小分子,在这里面真正要找到有差异化的项目,竞争美国市场,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一直认为耐心非常重要,不管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这条路我要一直坚持走下去。对于创新药到底选什么项目,什么方向,我认为基本上找不到一个固定模式思路,所以我们公司在创新药方向一直在探索,尝试各个不同的方向。目前我们创新药应该渐入佳境,第一个进入临床的项目,现在刚刚准备要启动三期研究,后续的项目我认为都是真正非常具有差异化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方向可能基本上没人在做。
改良药物剂型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就是从一个剂型改到另外一个剂型,你不管改哪个剂型,你必须对这个剂型有很深入透彻地了解,因为每个剂型有不同的临床使用环境,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快速释放、慢速释放、局部释放、靶向释放,你的临床需求在哪?根据临床需求,我们再选择哪些剂型适合做这些东西,再在剂型上我们再看哪些制剂技术可以让它更好地展现,这是逻辑性问题。从临床推到你对制剂的了解,从制剂推到你的制剂技术,从制剂技术推到你的人才资源储备,其实我觉得产品也就可以做了,我觉得这个产品如果真的是以临床需求,以对剂型的特殊了解,以及你的制剂技术非常好的话,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有的。
如何利用改良新药技术优化毒麻类和放射药,并为企业提供介入该领域的建议和思路?
其实我参与过两个品种的研发,一个是麻醉药品,还有一个就是戒毒药的研发。我觉得因为这类领域里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而且有准入制门槛的限制,所以相比较而言,这类品种可能市场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参与的选手比较少,反而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市场回报,大家如果能有这样的资质可能做这样的工作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逻辑。
举个例子,纳曲酮这个药物是对吗啡成瘾的瘾君子口服给药以后吸吗啡就不嗨了,这个药虽然口服给药疗效非常好,但是你要盯着瘾君子每天服纳曲酮,他就不愿意或者他会各种逃避。现在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皮下埋置,纳曲酮埋下去以后埋一次管五个月到半年,瘾君子吸了毒品以后也不嗨了,依从性会大大提高,这也改变了临床的重点指标,就是复吸率,口服的复吸率会很高,但是埋置以后复吸率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巨大临床价值的药品,如果能把它做成,对我们中国的戒毒戒来说是一大好事情。
高端复杂制剂是否具有仿制价值?
确实有药可以仿,比如首仿,我觉得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你也不见得仿得出来。我觉得你能做新,你一定要做新,在国外很多仿制药都是印度人一家仿出来十几家都仿出来了,如果你要做新药,那就有3-5年的市场独占期。
所以我觉着要从多方面考虑,一个是投入,一个是你产出这个产品有多少技术壁垒,如果你技术壁垒高了,你可以挺十几二十年都可能,确实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主张你能新,你就不要仿。第一个你仿得很费劲,而且你仿出来之后,大家都仿出来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能新则新,因为新有它的独占权,也有它的技术壁垒。
在高端复杂制剂研发中,应该选择仿制成熟产品还是进行改良创新?
作为一个在医药界做了很长时间的,我宁愿做二类创新药,不做仿制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仿制药特别对复杂制剂来说很难,他不比做一个新药容易,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挑战,甚至金钱上,也不见得省钱。因为仿照他已经有一个槛放在那,你做得不能比他好,也不能比他坏。我在回国以前都是做吸入创新药的,后来回来全做的仿制药,我才发现我对制剂的理解是来源于仿制药,而不是创新药。因为做创新药的时候你是不考虑那么复杂的,你考虑他的物理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疗效就可以了,但是当你做仿料才发现为什么要加这个辅料,其实有时候加辅料,在原研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
原来我们在国外做吸入的时候,有时候会加上一点表面活性剂,纯粹是为了绕开专利,但是当你拿到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为了绕开专利,这时候你拼命地研究他为什么加表面活性剂。其实加了表面活性剂以后,对他的肺部分布和吸收真有影响,但是做创新药我不考虑他,我只是考虑避开专利,但是到做仿制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区别对它是有影响,所以说做高端仿制药的BE是很难做的,做完以后一般对于吸入制剂来说,还要做临床,这个在时间上、金钱上不是特别省,有时候做二类创新药反而稍微好点,因为他没有标杆。
但是当你选择做二类新药,立题就很重要,你怎么来保证比他好?所以不管做仿制药还是做创新药,首先有几个一定要关注的。第一,你必须有技术平台的储备,对于复杂制剂的时候,没有一个平台的储备,你不管是仿制药还是创新药都做不出来的。第二,你必须有人才的储备。第三,还要有资源的储备,资源包括法规注册、临床前、临床的一些研究。还有资金的储备。对于高端复杂制剂来说,不管是仿制药还是创新药,这几个都是需要的。
做仿制药面临着BE等效性问题,而做创新药就面临着立项临床优势的问题,这个临床优势不是你设计出来的,而是你发现出来的,换句话就是你要对他的上市品种有全面的了解,无论是PK特征,还是临床一系列的表现,在这基础上能够克服,那就做二类创新药,但是我如果发现这类东西再做也改变不了多少,那我觉得你做二类创新药,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意义不大,倒不如花时间做仿制药。
在投资高端复杂制剂平台(如脂质体)时,应优先选择仿制国际成熟产品还是直接进行改良创新?
因为我本身是药大的老师,同时我也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一个临床CRO企业,目前我们做了高端制剂的探索性临床很多项目,我了解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的研发现状,我觉得一定要在CMC技术层面有个长期的积累,能够做到收放自如。不但要有工业化的成熟稳定的生产能力,还要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的放大能力,更要有一个关键处方工艺、关键质量标准和体内暴露水平之间关系的生物药剂的研发能力。所以工业药剂、物理药剂和生物药剂这三个合在一起才是真正产业化高端制剂平台的内涵,所以这块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是要经过长期的积累。
第二个,就是每一个药我有了技术特征、给途径特征以后,还是要找合适自己有针对性的品种我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恰好这个药物的药代特征、安全特征和有效性特征,适合我这个技术平台。对已上市药物特征的理解和不足的调研,两者的结合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高端制剂,拥有很好的CMC门槛,有高临床价值,才会真正获得高的市场回报,所以按照我的理解,没有一个捷径。
如何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临床试验并控制研发成本?
我看到群里也在问“我怎么能够少做临床呀?我怎么能够省钱呀?”我觉得这里面不是省钱少做的问题,如果你抛不开这个思路,势必就造成内卷,不管是二类新药,甚至一类新药也内卷,内卷就内卷在这方面,他们不是抱着一个做药的思路去做,而是抱着投机的思想去做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不合适的。
关于这个钱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有大钱,你可以多做几个项目,做得快一些,但如果你钱少,觉得这个药还挺好,那就慢工出细活,再往前走,我觉得只要你看好这个东西,钱多有钱多的做法,钱少有钱少的做法,但是我的理念是一定是我要做药,而不是投机取巧的做药。
原创报告
独家原创专业报告,有深度,有广度,深度解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底层逻辑和未来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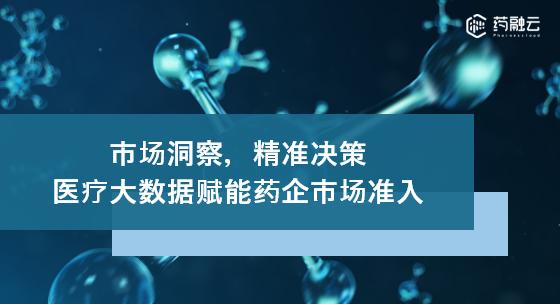 页数: 38
页数: 38
市场洞察,精准决策丨医疗大数据赋能药企市场准入
药融咨询
38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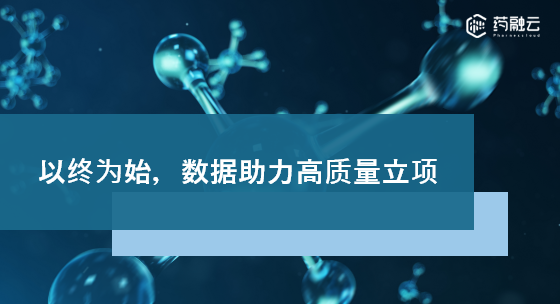 页数: 26
页数: 26
以终为始 ,数据助力高质量立项
药融咨询
26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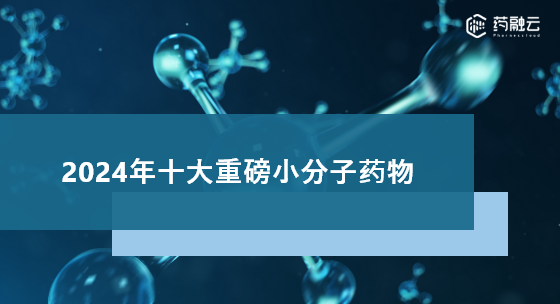 页数: 45
页数: 45
2024年十大重磅小分子药物
药融咨询
45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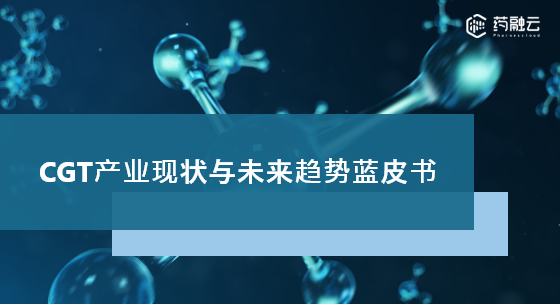 页数: 45
页数: 45
CGT产业现状与未来趋势蓝皮书
药融咨询
45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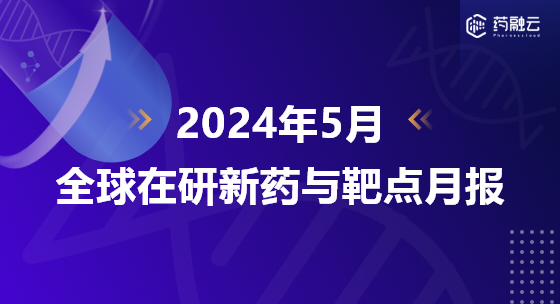 页数: 49
页数: 49
2024年5月全球在研新药与靶点月报
药融咨询
49
2024-0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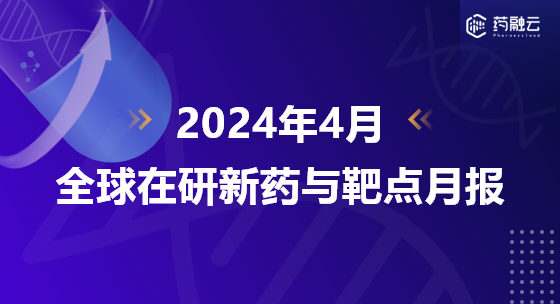 页数: 51
页数: 51
2024年4月全球在研新药与靶点月报
药融咨询
51
2024-0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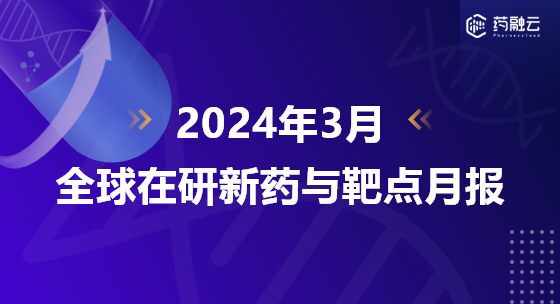 页数: 49
页数: 49
2024年3月全球在研新药与靶点月报
药融咨询
49
2024-0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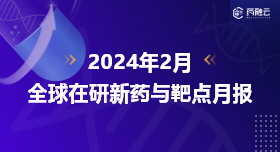 页数: 51
页数: 51
2024年2月全球在研新药与靶点月报
药融咨询
51
2024-0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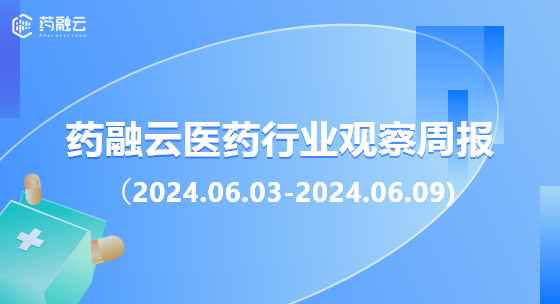 页数: 23
页数: 23
药融云医药行业观察周报(2024.06.03-2024.06.09)
药融咨询
23
2024-0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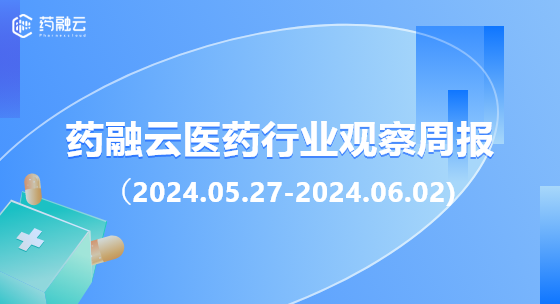 页数: 24
页数: 24
药融云医药行业观察周报(2024.05.27-2024.06.02)
药融咨询
24
2024-0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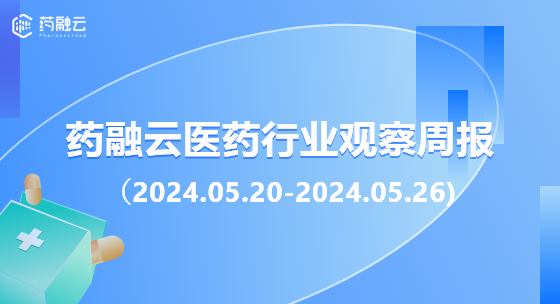 页数: 27
页数: 27
药融云医药行业观察周报(2024.05.20-2024.05.26)
药融咨询
27
2024-0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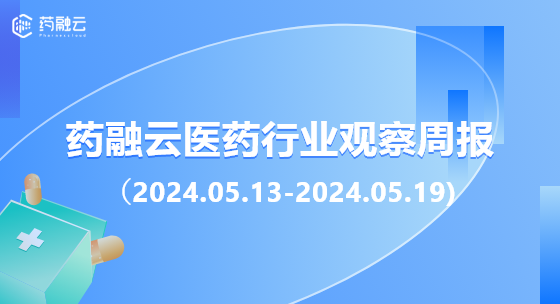 页数: 24
页数: 24
药融云医药行业观察周报(2024.05.13-2024.05.19)
药融咨询
24
2024-0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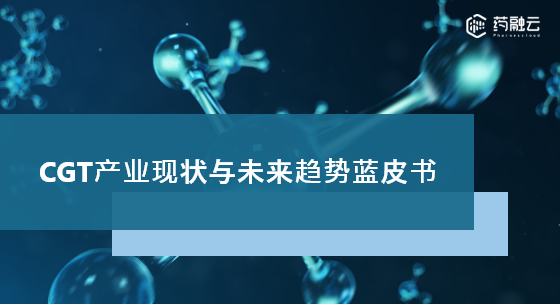 页数: 45
页数: 45
CGT产业现状与未来趋势蓝皮书
药融咨询
45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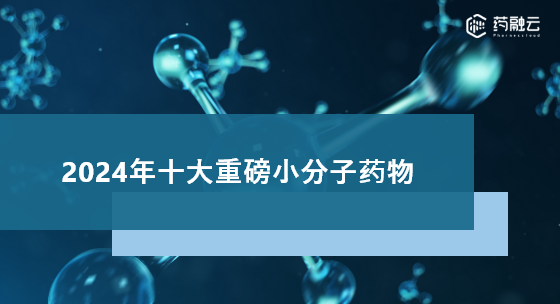 页数: 45
页数: 45
2024年十大重磅小分子药物
药融咨询
45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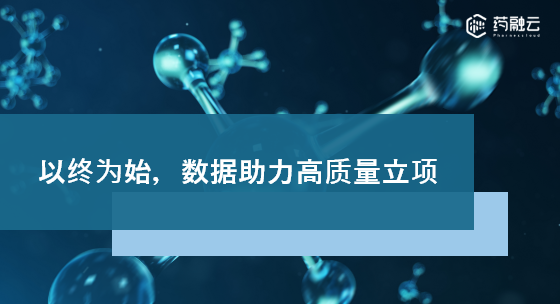 页数: 26
页数: 26
以终为始 ,数据助力高质量立项
药融咨询
26
2024-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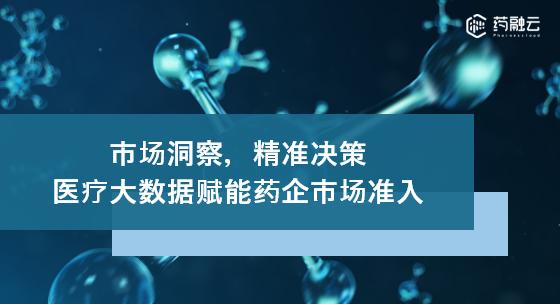 页数: 38
页数: 38
市场洞察,精准决策丨医疗大数据赋能药企市场准入
药融咨询
38
2024-06-17